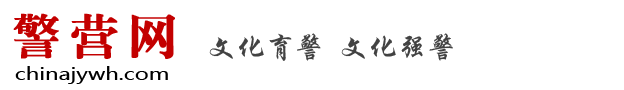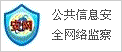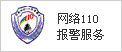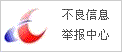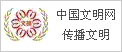文学与生命的双重证词
书里书外
文学与生命的双重证词
文学与生命的双重证词
《我在场》 作者:阎纲 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出版时间:2025年3月
■雷焕
当鲐背之年的阎纲先生以《我在场》为精神坐标,将七十余载文学生涯凝结成沉甸甸的文字时,这部作品早已超越了普通散文集的范畴。这是一位世纪老人以血肉之躯丈量时代沟壑的实录,更是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自白。在泛黄的历史褶皱与鲜活的当下叙事之间,阎纲以“在场者”的清醒姿态,为当代文学史浇筑了一座兼具温度与重量的纪念碑。
翻开《我在场》,扑面而来的是文字的呼吸感。书中收录的篇章看似散落如星,实则暗含经纬:既有对柳青、路遥等文学巨匠创作现场的追忆,亦有对《白鹿原》《平凡的世界》等经典文本的切片式剖析;既有通过文献考据与亲历者口述重构历史现场,让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历史细节重现,也有对当下文化现象的冷峻观察。阎纲像一位手持时光棱镜的勘探者,将个人记忆与集体经验交织,让文学史中那些被教科书简化的瞬间重新鲜活。当他在《三十八朵荷花》中写女儿离世时,笔尖流淌的不仅是父亲的哀恸,更是一个作家对生命尊严的终极叩问——这种将私人痛感升华为公共思考的能力,正是其文字穿透时空的密钥。
阎纲的“在场”绝非简单的见证,而是以肉身介入历史的姿态。在《人民文学》编辑部亲历“伤痕文学”破土而出的时刻,他既是编辑又是评论家,既为作品问世开疆拓土,又以犀利文字为其正名。这种双重身份赋予其写作独特的张力:既有亲历者的体温,又保持审视者的锐利。书中对“改革文学”思潮的梳理,既能看到社会政策在作家笔下的嬗变轨迹,也能触摸到普通工人面对时代转型的惶惑与期待。这种将文学现象置于社会肌理中的解剖,使文本成为折射时代精神的三棱镜。
相较于学院派的理论架构,阎纲的在场书写更具生命的粗粝感。他写吴冠中在牛棚里偷画速写时,“手指冻得通红,却比炉火更灼热”;记录韦君宜病榻上修改《露莎的路》时,“颤抖的笔迹里藏着未烬的火种”。这些细节如同文学史的毛细血管,让宏大的历史叙事有了可触可感的血肉。尤为珍贵的是,面对文坛浮沉,他始终保持着“说真话”的勇气。在商业写作泛滥的当下,他直言“带体温的文字才是对抗虚无的良药”,这种坚守让《我在场》成为喧嚣时代里一剂清醒剂。
书中对乡土中国的凝视,恰是阎纲精神原乡的投射。当他在礼泉县的黄土地上讲述“中国的故事”时,笔下的关中平原既是地理坐标,更是文化隐喻。《我还活着》中那些关于饥荒年代的故事,在《我在场》里发酵成更深层的思考:现代化进程中,乡村该如何守护自己的精神根系?这种追问不是怀旧式的挽歌,而是站在历史裂变处的忧思。正如他在书中写道:“每个作家的故乡都在沦陷,但文字能让它重生。”这种将个体经验转化为文化自觉的书写,使作品获得了超越地域的价值。
在碎片化阅读蚕食思考深度的今天,《我在场》的存在本身即一种宣言。当九旬老人仍以“鲐背之年的冲锋”姿态写作时,他不仅在对抗时间的消解,更在重塑文学与生命的关系。书中那些“熔铸个人记忆于时代叙事”的文字,既是对过往的致敬,亦是对未来的邀约——当我们跟随他的笔触重返《创业史》的创作现场,凝视《人生》的手稿修改痕迹时,触摸到的不仅是文学史的筋骨,更是一个民族精神生长的年轮。
这部作品最动人的力量,或许在于它证明了真诚的写作永不衰老。阎纲用“眼见为实,实话实说”八个字构筑的文学观,在流量至上的时代宛如孤帆远影。但正是这种固执的在场,让文字获得了穿越时空的重量。当最后一页合上,留在读者心中的不仅是文学史的吉光片羽,更是一个知识分子在沧海横流中始终挺立的背影——这或许就是《我在场》给予当代文坛最珍贵的启示:真正的写作,从来都是生命与时代的双重在场。
本文来源:西安日报责任编辑:
免责声明:
1、凡本网注明“来源:***(非中国警营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的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2、如因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需要同本网联系的,请在30日内进行。
- 2025-07-01文学与生命的双重证词
- 2025-06-30填补国内科幻研究手册空白,渝版图书《科幻文学研究手册》首发
- 2025-06-27“人民文学奖”为何给科幻戏剧《云身》新设奖项?
- 2025-06-26网络文学向新而行
- 2025-06-25【文学里念故乡】我用小说再造故乡
热点推荐
精选图文
阅读排行榜
品牌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