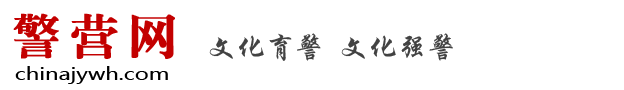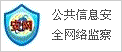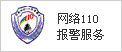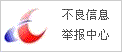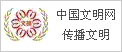呼唤“在场”的文学批评
2020-08-07 14:18:56
来源:河北日报
责任编辑:王力平
在现代文学发展中,理论批评的“在场”,发挥着重要的基石作用。中国新文学的主潮,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不是对于大众阅读需求的温顺回应,不是为了满足流行趣味而生产的文化消费品。中国新文学是由一群思想先驱发起的,以科学、民主为旗帜,以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为目标,以实现国民思想启蒙、文化批判、审美教育和政治动员为己任的文学创造。而要真正担起这一责任,实现这一目标,中国新文学又必须是“大众化”的。
在文学领域有两种不同的文学研究。一种是把一个特定的、独立的文学现象(作家、作品、文学思潮流派等),作为静态的研究对象,研究的目的是“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回答“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完成这样的研究,对象的“静态”特征、对象的稳定性十分重要。在这种研究中,首先,对象最好是“完成时态”,以减少变化的可能;其次,对象应具“原典性”,以减少“阐释”可能带来的歧义。所以,观察学科齐备的高校中文系可以发现,古典文学研究地位最高,现代文学研究次之,当代文学研究又次之。在古典文学研究中,先秦文学地位最高,两汉魏晋唐宋次之,元明清又次之。
还有另一种文学研究,同样要完成“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的任务,回答“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但不同的是,研究并没有到此为止,进一步的任务是,将这个“然”与“所以然”,“是什么”和“为什么”归在一起,名之曰“实然”,之后还要继续回答,或者至少还要继续提出“或然”与“应然”的问题。显然,在这种研究中,对象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发展的、变化的。从根本上说,这种研究不承认自己面对的文学现象是已然完成的、静态的和不可改变的。它坚持把对象放在社会历史和社会审美意识发展的过程中去考察。它关心如何认知一个“点”,如何感知和展开这个“点”所具有的内在的丰富性,同时,它也关心这个“点”在社会历史和社会审美意识背景下,或然与必然的运动轨迹。
如果说,前一种研究具有“学术性”,后一种研究则不仅是学术性的,同时还具有实践性的品质。换言之,这种研究的任务,不仅在于如何解释面前的文学世界,还在于如何改造这个世界,如何为当代文学的发展开辟道路。这种研究是进入文学创造现场的、具有“现场”意识的研究,是具有较强实践性的学术活动。只是在习惯上,我们将前一种研究称作“学术活动”,而把后一种研究称作“批评活动”。
那些进入文学现场的、具有强烈实践品质的思想理论和文学评论,总是不断地为文学创作开辟着道路。
在现代文学发展中,理论批评的“在场”,发挥着重要的基石作用。中国新文学的主潮,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不是对于大众阅读需求的温顺回应,不是为了满足流行趣味而生产的文化消费品。中国新文学是由一群思想先驱发起的,以科学、民主为旗帜,以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为目标,以实现国民思想启蒙、文化批判、审美教育和政治动员为己任的文学创造。而要真正担起这一责任,实现这一目标,中国新文学又必须是“大众化”的。这是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构成了中国新文学发展的“二重性”。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都可以从新文学的这种“二重性”中得到说明。
乡土文学是新文学发展的重要收获。乡土文学的理论倡导和创作实践,一方面是新文学获得“土气息”“泥滋味”,实现大众化的努力;另一方面,它又是基于现代性视野的乡土忧思和批判,是站在现代性高地上,对中国乡土现实的审美发现、文学想象和形象描写。
在乡土文学的发展过程中,理论批评的“在场”,表现为胡适、陈独秀、李大钊对于“新文学”的推动;表现为周作人对于“平民文学”,对于地方色彩、民俗风情的倡导;表现为茅盾对于“农民小说”“农村小说”的理论思考;更表现为鲁迅对于乡土文学的批评阐释。
显然,理论批评的“在场”,不仅为乡土文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并且进一步将忧思、启蒙与批判的主题确立为乡土文学的核心价值。新时期以来,虽有重写文学史的努力且不乏实绩,但终不能移动其地位,就因为此一文学主题实乃新文学的主题、时代的主题。
多年来,基于重建文学审美价值的内在需求,也由于解构主义理论和“新批评”思潮的影响,倡导“细读”,主张“回到文本”,已成为文学批评的自觉意识。其实,如果不考虑“回到文本”背后的哲学理论背景,对于“语言”“文本”的自觉,中国文学是在魏晋时代完成的。在音律声韵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是沈约的“四声八病”理论,对于五言诗歌向格律诗的过渡和发展,是一个重要的贡献。语言形式对于诗、词、曲的演变所具有的意义不去谈了。在发生和发展更为晚近的小说研究中,李卓吾评点《西游记》、毛宗岗评点《三国演义》、金圣叹评点《水浒传》、张竹坡评点《金瓶梅》、脂砚斋评点《红楼梦》,都是基于作品文本的小说叙事研究。
不过,说这些不是为了证明“从前阔”。是想说这种自觉意识,可能会遮蔽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即“回到文本”的努力,日益演化为“囿于文本”的局限。事实上,真正的文学批评,应该是回到文本,但不囿于文本。囿于文本的批评和脱离文本的批评一样糟糕。
鲁迅在谈到文学批评时曾说:“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他说的是家常话,但其中的含义是清晰真切的。
一是“坏处说坏,好处说好”。这句话涉及批评的态度,也涉及批评的品质。“坏处说坏,好处说好”,存善意,说真话。不“捧杀”也不“棒杀”。这是批评的态度。所谓“品质”,是指批评的学术品质。无论说“好”说“坏”,总要说到肯綮处,说出“好”在何处,“坏”在何处,有科学的分析和准确的判断,而不是隔靴搔痒,言不及义。
二是“于作者有益”。所谓“于作者有益”,实质是于作者的创作有益。所以,这个“作者”,可以是具体作品的写作者,也可以是更广泛的当代文学创作实践。换言之,就是批评要介入创作实践,于作者、于创作有益。这意味着,一个负责任的批评家,不会割裂作品与时代、与社会生活的联系,也不会把“作者已死”奉为圭臬。
把“批评”置于社会生活和当代文学创作实践的双重背景下,在“写什么”和“怎么写”的不同领域,与创作构成“对话”关系;进而与创作一起,与社会生活、与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的历史实践构成审美的“对话”关系,是令人期待的批评的“在场”。(王力平)
在文学领域有两种不同的文学研究。一种是把一个特定的、独立的文学现象(作家、作品、文学思潮流派等),作为静态的研究对象,研究的目的是“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回答“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完成这样的研究,对象的“静态”特征、对象的稳定性十分重要。在这种研究中,首先,对象最好是“完成时态”,以减少变化的可能;其次,对象应具“原典性”,以减少“阐释”可能带来的歧义。所以,观察学科齐备的高校中文系可以发现,古典文学研究地位最高,现代文学研究次之,当代文学研究又次之。在古典文学研究中,先秦文学地位最高,两汉魏晋唐宋次之,元明清又次之。
还有另一种文学研究,同样要完成“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的任务,回答“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但不同的是,研究并没有到此为止,进一步的任务是,将这个“然”与“所以然”,“是什么”和“为什么”归在一起,名之曰“实然”,之后还要继续回答,或者至少还要继续提出“或然”与“应然”的问题。显然,在这种研究中,对象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发展的、变化的。从根本上说,这种研究不承认自己面对的文学现象是已然完成的、静态的和不可改变的。它坚持把对象放在社会历史和社会审美意识发展的过程中去考察。它关心如何认知一个“点”,如何感知和展开这个“点”所具有的内在的丰富性,同时,它也关心这个“点”在社会历史和社会审美意识背景下,或然与必然的运动轨迹。
如果说,前一种研究具有“学术性”,后一种研究则不仅是学术性的,同时还具有实践性的品质。换言之,这种研究的任务,不仅在于如何解释面前的文学世界,还在于如何改造这个世界,如何为当代文学的发展开辟道路。这种研究是进入文学创造现场的、具有“现场”意识的研究,是具有较强实践性的学术活动。只是在习惯上,我们将前一种研究称作“学术活动”,而把后一种研究称作“批评活动”。
那些进入文学现场的、具有强烈实践品质的思想理论和文学评论,总是不断地为文学创作开辟着道路。
在现代文学发展中,理论批评的“在场”,发挥着重要的基石作用。中国新文学的主潮,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不是对于大众阅读需求的温顺回应,不是为了满足流行趣味而生产的文化消费品。中国新文学是由一群思想先驱发起的,以科学、民主为旗帜,以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为目标,以实现国民思想启蒙、文化批判、审美教育和政治动员为己任的文学创造。而要真正担起这一责任,实现这一目标,中国新文学又必须是“大众化”的。这是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构成了中国新文学发展的“二重性”。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都可以从新文学的这种“二重性”中得到说明。
乡土文学是新文学发展的重要收获。乡土文学的理论倡导和创作实践,一方面是新文学获得“土气息”“泥滋味”,实现大众化的努力;另一方面,它又是基于现代性视野的乡土忧思和批判,是站在现代性高地上,对中国乡土现实的审美发现、文学想象和形象描写。
在乡土文学的发展过程中,理论批评的“在场”,表现为胡适、陈独秀、李大钊对于“新文学”的推动;表现为周作人对于“平民文学”,对于地方色彩、民俗风情的倡导;表现为茅盾对于“农民小说”“农村小说”的理论思考;更表现为鲁迅对于乡土文学的批评阐释。
显然,理论批评的“在场”,不仅为乡土文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并且进一步将忧思、启蒙与批判的主题确立为乡土文学的核心价值。新时期以来,虽有重写文学史的努力且不乏实绩,但终不能移动其地位,就因为此一文学主题实乃新文学的主题、时代的主题。
多年来,基于重建文学审美价值的内在需求,也由于解构主义理论和“新批评”思潮的影响,倡导“细读”,主张“回到文本”,已成为文学批评的自觉意识。其实,如果不考虑“回到文本”背后的哲学理论背景,对于“语言”“文本”的自觉,中国文学是在魏晋时代完成的。在音律声韵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是沈约的“四声八病”理论,对于五言诗歌向格律诗的过渡和发展,是一个重要的贡献。语言形式对于诗、词、曲的演变所具有的意义不去谈了。在发生和发展更为晚近的小说研究中,李卓吾评点《西游记》、毛宗岗评点《三国演义》、金圣叹评点《水浒传》、张竹坡评点《金瓶梅》、脂砚斋评点《红楼梦》,都是基于作品文本的小说叙事研究。
不过,说这些不是为了证明“从前阔”。是想说这种自觉意识,可能会遮蔽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即“回到文本”的努力,日益演化为“囿于文本”的局限。事实上,真正的文学批评,应该是回到文本,但不囿于文本。囿于文本的批评和脱离文本的批评一样糟糕。
鲁迅在谈到文学批评时曾说:“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他说的是家常话,但其中的含义是清晰真切的。
一是“坏处说坏,好处说好”。这句话涉及批评的态度,也涉及批评的品质。“坏处说坏,好处说好”,存善意,说真话。不“捧杀”也不“棒杀”。这是批评的态度。所谓“品质”,是指批评的学术品质。无论说“好”说“坏”,总要说到肯綮处,说出“好”在何处,“坏”在何处,有科学的分析和准确的判断,而不是隔靴搔痒,言不及义。
二是“于作者有益”。所谓“于作者有益”,实质是于作者的创作有益。所以,这个“作者”,可以是具体作品的写作者,也可以是更广泛的当代文学创作实践。换言之,就是批评要介入创作实践,于作者、于创作有益。这意味着,一个负责任的批评家,不会割裂作品与时代、与社会生活的联系,也不会把“作者已死”奉为圭臬。
把“批评”置于社会生活和当代文学创作实践的双重背景下,在“写什么”和“怎么写”的不同领域,与创作构成“对话”关系;进而与创作一起,与社会生活、与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的历史实践构成审美的“对话”关系,是令人期待的批评的“在场”。(王力平)
本文来源:河北日报责任编辑:王力平
免责声明:
1、凡本网注明“来源:***(非中国警营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的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2、如因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需要同本网联系的,请在30日内进行。
相关阅读
- 2023-05-15《文选》是本什么书?(子曰诗云)
- 2023-05-12细节的层次、功能与锤炼
- 2023-05-11《孙犁年谱》:读来文字带芳鲜
- 2023-05-10书写昆虫与人们相处的诗意时刻——评散文集《小虫子》
- 2023-05-09深化文学与戏剧影视的纽带联系
头条图文
热点推荐
精选图文
阅读排行榜
品牌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