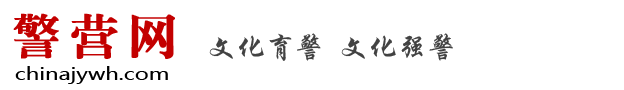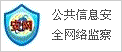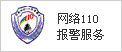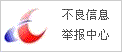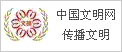从北平到东京:聂耳生命中的双城记和进行曲
2019-11-29 14:26:50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责任编辑:殷思佳
作者:殷思佳(四川美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日本东京大学访问学者);冯雷(北方工业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日本东京大学JSPS研究员。)
在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的鹄沼海岸,每年的7月17日都会有一支由日本青壮年组成的藤泽市消防音乐队郑重其事地演奏《义勇军进行曲》,为的是纪念在这里不幸溺水去世的中国作曲家聂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曲作者。1935年7月17日,聂耳在鹄沼海岸附近水域游泳时与世长辞,年仅23岁。在中日尚未建交的1954年,藤泽市民就为聂耳修建了纪念碑,此后几经风雨又几经重建、改建。不但如此,如今每个月的第一个周六上午都有不少中日友好人士相约到纪念广场来打扫卫生。八十多年过去了,聂耳已经成为中日民间友好交往的重要纽带。
矢志不渝,北上进京
乘北京地铁二号线到宣武门,西南口出站,沿着宣武门外大街奔南走,没多远在右手边闪出一条胡同,过去这里一直叫鞑子桥胡同,1965年雅化为达智桥胡同。进了胡同第一个丁字路口往南拐便是校场头条。和达智桥胡同的规整、干净相比,校场头条略逊色几分。路西的七号院离巷子口不远,宅门看起来平淡无奇,同资料照片里气派的广亮大门一比真是相形见绌,尤其是门口的两只石鼓和门簪子上“云南会馆”的匾额早已不见踪迹。1932年11月5日,披着这一年的初雪,聂耳在日记里写道:“北平!算是告了一段落吧!二次重来,不知又待何时?”依依不舍之情可见一斑。第二天下午,聂耳辞别才住了三个月的云南会馆,重返上海。
聂耳在北京的经历同他此前在上海的生活是无法割裂开的。从聂耳的“北平日记”来看,他1932年8月10号到了北平,仅住了十天就动了回上海的念头,在随后的几天里这个想法愈发按捺不住,几番下定决心,无论如何要在9月16号回上海去,为此还曾专门到正阳门车站问讯处打听发车时间、票价、行李等。那最后为什么在北平延宕下来,当初又为什么要来北平呢?
聂耳离开上海,最直接的原因是因为他化名“黑天使”写文章批评亦师亦友的黎锦晖,化名被识破之后,聂耳脱离了黎锦晖领导的明月歌剧社另寻出路。有的人认为这种描述实乃是尊者讳,掩盖了聂耳想要在《芭蕉叶上诗》等剧中扮演角色而未得,于是转而挥笔泄愤的隐情。这种说法流布甚广,但显然把聂耳想得太过狭隘和自私,而且也没有把聂耳的思想成长和转折看成是一个完整的链条,自然也就谈不上理解聂耳诸多看似一时冲动的选择。简单来说,聂耳的“上海日记”大致主要有四方面的内容:爱情烦恼、日常练琴、批评剧团以及自遣自励,后三者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在日记里,聂耳很少自暴自弃,他常常显得充满自信,认为自己可以胜任许多工作,包括在电影里扮演一些角色,并且事实上聂耳是有过从影经历的。另一方面他又时常进行自我教育,“不要忘记自己的发展”。但聂耳对明月歌剧社显然不太满意。1931年春,在初识田汉时聂耳便对黎锦晖“某些不健康、不严肃的倾向”表示了不满,在近一年的时间里他在日记中多次写到只是“帮他们工作”“干完这两年再说”“另走他路吧”,在1932年3月聂耳便萌生过去北平考“艺专”的想法。
聂耳对“明月社”的不满有管理、待遇方面的原因,更主要的还有艺术方面的原因。聂耳少年时曾参加过“学生军”,到上海之后常常以“革命新青年”“革命者”自诩,他时常思考“怎样去做革命的音乐”、如何“能够兴奋起、可以鼓动起劳苦大众的情绪”,他当时的朋友中不乏像于立群、贺绿汀、艾思奇、郁达夫、田汉这样的进步文化人,而黎锦晖却恰恰饱受所谓“靡靡之音”的批评。所以聂耳一方面出于上进之心希望扮演角色,另一方面又撰文批评,这其实并不矛盾,都是有思想脉络可循的。并且当时聂耳和周围一些关系密切的朋友之间不时会交换文章甚至是日记,聂耳动笔也并非头脑一热,而是看到好友金焰在《电影时报》上发表了文章而“一时激起我的发表欲,想对他来一个相继的意见”。由此可见,聂耳进剧社、写文章、上北京,这些正如同他成长道路上一系列前后相继的车站一般,并非临时起意。这样似乎就可以更加明确聂耳进京的意图:在思想上追求进步,在艺术上寻求提高,在个人前途上谋求发展。
聂耳住进云南会馆的当天就和在北平的朋友们取得了联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抵达北平之后的第三天,聂耳便去拜会了黎锦晖的四弟黎锦舒,两个人谈话多时,黎锦舒还建议聂耳到欧洲去。后来重回上海之后的第二天,聂耳就在曾被他批评过的卜万苍家中遇到了黎锦晖的七弟黎锦光的太太,日记里记载说:“七嫂子好像比以前活泼些,对我很有好感。”由此可见聂耳与黎锦晖及其周围亲友之间未见得已经闹得关系破裂、形同陌路。
中山公园、大栅栏、东安市场、什刹海、北海公园、北京动物园、双清别墅、香山饭店、卧佛寺、碧云寺、清华园、燕园……和今天的游客一样,聂耳也是先到这些地标景点玩了个遍。但他毕竟不是来旅游的,而是带着目标来的。从日记来看,聂耳一方面也希望能进正规大学系统学习,到北京20天后他的日记里便出现了周围朋友们投考学校的内容;但另一方面他在上海养成的自我激励、自我批评的心理又刺激他担心校园生活太过悠闲、使自己“软化下去”。两种心理此消彼长,难以决断。一度下定决心回上海也正是这种犹豫、焦虑心态的体现。读聂耳的日记时常会让我想到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其实聂耳的日记也正是一部更加贴近真实生活的“自叙传”,把20世纪30年代的聂耳同20年代的丁玲、莎菲放在一起,这或许会使人们更容易体会聂耳的烦躁、彷徨、忧虑和希冀,更容易在伟大和年轻之间恰切地想象聂耳。
北平是历史文化名城,经过“文学革命”的洗礼与“革命文学”的筛选,到20世纪30年代北平形成了阵容齐整的“京派”文人圈,他们追求艺术的醇正和恬静,批评低级趣味和商业竞买,特别是后者,正与聂耳相合。在朋友们的建议下,聂耳参加了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的入学考试,但是名落孙山。北平艺院前身为1918年创办的北京美术学校,此后历经变更,1928年改为北平大学艺术学院,1949年撤销。校址原位于西单京畿道,现在似乎已经湮没不存了。在放榜之前,聂耳找到了在东交民巷里栖身的白俄小提琴教师托诺夫,和他学习以期提高琴艺,断断续续持续到10月中旬,因学费难以为继而被迫终止。这些都是聂耳在北平耽搁下来的原因,而此外还有一些原因则是聂耳在日记中未曾多说也不便多说的。
1928年,聂耳在昆明时便秘密加入了共青团,到上海之后对革命文艺则更加关注,甫一住进云南会馆便引起了便衣特务马匡国的注意,此后聂耳在日记里则以“马三哥”代之。值得一提的是,在聂耳入住之前,云南会馆曾经是云南党组织创建过程中最早的基地。五四运动中,云南青年成立了“大同社”,1922年后,大同社成员多数潜入北京,在云南会馆里组织起“新滇社”,在此之后部分新滇社成员秘密入党并回云南创立了党组织。今天在校场头条胡同口的简介里对这段历史也略有提及。
当然同样关注着聂耳的还有地下党组织,特别是“北平左翼戏剧家联盟”,上海方面也给北平剧联的负责人寄来了关于聂耳的介绍信。在北平剧联的吸纳和引领之下,聂耳积极参与了不少进步的文艺活动。在落榜之后,为北平剧联的机关报《戏剧新闻》写稿、参加文艺演出,尤其是作为主要负责人筹建“北平左翼音乐家联盟”成为聂耳在北平的主要活动。特别是在朋友的影响下,聂耳的创作欲再度躁动起来,计划以他“由云南至广、湖的实际生活为取材,写成一篇长篇小说”,并在日记里列了一份大纲。他还把自己和同乡诗人柯仲平做了比较,认为:“说起云南的柯仲平的创作精神,使我觉得自己也可能做出和他差不多的作品,我有的是充分的材料。”只可惜天妒英才,假以时日的话聂耳未尝不会在文艺批评乃至文学创作领域开拓出一片天地来。
北上之行虽然只有区区三个月,但是对聂耳来说却可谓影响深远。直观地来看,离开北平之后,聂耳的日记较之以往稀疏了许多,1933年常常是一连几日都付之阙如,1934年和1935年留日之前各只记了三天。而在音乐创作和著述上,聂耳则迎来一个明显的高峰,特别是在音乐创作方面,日后人们耳熟能详的《开矿歌》《卖报歌》《毕业歌》《梅娘曲》《金蛇狂舞》等全都作于聂耳离开北平之后。显见得聂耳在艺术创作上更加投入了,他甚至觉得“写信比写日记重要”。
更为隐蔽和内在的是,聂耳在思想上更加成熟了,在1932年11月7日离开北平之后,1933年初由赵铭彝、田汉做介绍人,夏衍监誓,聂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更加深入地参加到“左联”领导下的文艺工作中来,这或许才是聂耳转变的内在驱动力。如果说是摩登的上海为聂耳提供了最华丽的舞台的话,那质朴的北平给予聂耳的“挫折教育”则助力这位天才的音乐家拉开了人生舞台上那掩饰了许多未知与可能的神秘大幕。
聂耳是因为躲避抓捕而于匆促之间赴日的,但赴日其实也一直是聂耳的梦想。在云南读书时,聂耳便选修过日语,在北平落榜之后前途渺茫之际聂耳也曾憧憬过到日本去,但因为没有钱而打消了念头。除却个人方面的原因之外,到日本去还与晚清以来的诸多社会因素有关,最主要的是甲午一战带给中国的莫大刺激,举国上下皆谓守旧不变终非长计。当然清政府也有许多顾虑,唯恐过分摄取西学而影响自身政体的安危,较之欧美,“地属同洲政体民情最为相近”的日本就成为最适宜的对象,因之制定了一系列留学政策。张之洞在《劝学篇》里辩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各种西学书之要者,日本皆以译之,我取径于东洋,力省效速”。梁启超也认为日文音少、无棘刺扞格之音、文法疏阔、名物象事多与中土相同、汉文居十六七,所以学习日文要更为容易。此外,留学日本“文同、地近、费省”也是颇为实际的因素。在这些之外,也不能忽视日本官绅在中国的热心延揽,只是在“维持东亚经纶之大策”的包装之下掩藏着的却是文化殖民的祸心。在多重因素的合力之下,虽然“读的是西洋书,受的是东洋气”,但赴日留学者仍然浩浩荡荡,最多时一年有八千余人,在聂耳赴日的1935年还出现了约6500人的小高峰。日本方面也相应设立了许多为中国留学生而办的学校,例如培养了一众日后知名人物的成城学校、弘文学院、振武学校以及聂耳就读的“东亚高等预备学校”。
比起当初到北平时先是游玩了一番,聂耳抵达东京的当天就到“东亚”听了两个小时的日语课,第二天就报了名入学。其实当看到聂耳是在“东亚”补习日语时,我不禁在心里暗暗画了个惊叹号,因为1936年萧红到东京后也是在这个学校上课,略长半岁多的萧红还要管聂耳喊一声“学长”。这样一来,这个东亚学校自然就成为不得不去看一看的所在。
经查,东亚学校后来毁于地震,原址已经改为“全爱公园”,位于东京都千代田区神田神保町二丁目,离东京大学并不太远,导航显示步行二十来分钟就能走到。东京的街道比起北京要狭窄得多,尤其是导航规划的步行优化路线,马路更显逼仄。在异国他乡苦心孤诣地寻访先辈同胞的足迹则更有一番难以道尽的感受。几番曲曲折折之后,全爱公园终于闪现出来。名曰公园,实际上非常袖珍,一个喷泉、两个花坛、几棵树木而已。花坛里竖着一碑、一牌。石碑上端醒目地刻着“周恩来曾在此求学”;下端则表明这里便是“东亚高等预备学校遗迹”。旁边的牌子上用日汉双语简要介绍了“日中两国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东亚学校读书的经过,落款是“千代田区日中友好协会”。原来周恩来、聂耳、萧红都曾在这里学习过。我忽而想到那难以道尽的感受中或许包含着“抗拒遗忘”之意。
除了东亚学校之外,聂耳还曾到“日比谷公会堂”“东宝剧场”“九段军人会馆”“新宿第一剧场”等地观摩过许多文艺演出,这几处相距都不太远,我也都一一专门去找过,有的仍然耸立在街头,有的则已经毁弃并随着时间渐渐被人淡忘了。
提起聂耳,人们最直接想到的恐怕便是《义勇军进行曲》,鲜为人知的是,《义勇军进行曲》是聂耳在东京修改定稿的。当时地下党领导下的“电通影片公司”筹拍新片《凤凰的再生》,由田汉编剧。但田汉刚写出一个故事梗概和主题歌歌词便被捕入狱了,夏衍继续把故事梗概写成电影文学剧本,并改名为《风云儿女》。行将避难的聂耳得知消息后主动请缨为主题歌作曲,他在上海完成初稿,抵达东京之后加工修改,寄回国内。田汉后来听到这支曲子,盛赞聂耳的作曲“爽朗明快,善于处理在别人很不易驾驭的词句,这歌词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是被认为很不容易驾驭的,而他处理得很自然有力。”在谱曲之外,聂耳还结合音乐旋律对田汉的原作做了一些调整,尤其是在“我们万众一心”之前三呼原稿开篇的“起来”,强化了步步高涨的气势。
然后在历史的氧化作用下,有些细节却渐渐涣漫不清了。有不少文章包括田汉本人都引用了孙师毅的回忆,说《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是写在一张包香烟的锡纸的衬纸上。而夏衍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纠正说田汉的《入狱》才写在这种衬纸上,是田汉记错了。田汉的剧本梗概“写在旧式十行红格纸上,十余页。《义勇军进行曲》这首主题歌,写在原稿的最后一页,因在孙师毅同志书桌上搁置了一个星期,所以最后一页被茶水濡湿,有几个字看不清楚。”如果说这种错讹与当时动荡的社会环境和当事人的记忆偏差有关,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另有些明显的错误则实在令人费解。有不少资料里都把聂耳和同乡好友廖伯民的合影错当作是聂耳与田汉的合影,以讹传讹。事实上,田汉留下来的照片非常多,而且田、廖二人面貌差异明显,稍加辨认即当错不至此。我在东京有幸遇到田汉的后人,经过询问确认聂廖合影中的不是田汉。
从日记可以看得出,聂耳到日本之后时间上利用得非常紧凑,日记中也时常蹦出几个日文单词来。聂耳制定了四个“三月计划”,到日本两个多月的时候,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愉快地通报自己以学习日语为主的第一个“三月计划”“仅仅两月功夫便全部实现”。在东京,聂耳在音乐、戏剧和电影方面都做了不少深入的调查和总结,从他遗留的著述可以看出,聂耳在坚持左翼革命文艺立场的同时,汲汲于了解国外同行的技艺创新、潮流动向,这和他在国内时的思想发展是一脉相承的。如果不是天不假年,那么这段海外之旅完全有可能成为聂耳在艺术上新的酝酿期和孵化期。按照原计划,一年之后聂耳还打算到苏联、欧洲去。但是到日本才刚刚三个月,聂耳却因为一场意外在日本成为永远的不归之客。
说实话,“不归之客”这个词我还是在藤泽的聂耳纪念广场的碑文中第一次见到。1950年,日本马克思主义者福本和夫从英文版的《人民中国》上看到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以及聂耳的报道,他请藤泽市议员叶山冬子翻译了这篇报道和《义勇军进行曲》歌词。聂耳及其在藤泽市的活动于当地得以传播开来。同年11月,“聂耳纪念之夜”活动在藤泽市举行,《义勇军进行曲》在聂耳殒没的地方奏响。1952年福本和夫首倡为聂耳竖立纪念碑,1954年纪念碑落成。从1896年清政府选派首批13名留日生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四十年间负笈东游者至少在95000人,而日本为之塑像立碑者却屈指可数,聂耳正是其中之一。然而在1958年“狩野川”台风中纪念碑却被巨浪卷走了。藤泽市民于1963年成立了聂耳纪念碑保存会,重新筹建纪念碑。纪念碑原来位于引地川河口,可用之地狭窄,1965年新纪念碑在现在的位置落成,此后历经翻修、扩建,形成了现在聂耳纪念广场的形制和规模。
广场背倚相模湾,不远处就是著名的景点江之岛,不少人在近海处冲浪、嬉戏,还有许多人在广场周围的沙滩上烧烤、打球,乌鸦和老鹰自由地飞翔在天空上,周围的气氛非常轻松、惬意。现如今,广场上共有六块各具来历的碑铭,其中一块是由1986年时任藤泽市长的叶山峻题写的《聂耳纪念碑的由来》。可能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位叶山峻的母亲就是当年翻译《义勇军进行曲》的叶山冬子。两代人前仆后继、薪火相传,这使得聂耳纪念碑更具纽带意义,不但连接着中日两国,同时也连接着日本国内的友好人士。
在纪念广场中央竖立着一座造型奇特的祭台,仔细一看,祭台的平面乃是一个“耳”字的造型。在学艺的过程中,人们发现聂耳别具耳聪,听得出、记得住、弹得来,所以戏称他“耳朵”。在当时“聂”字用繁体写作“聶”,“聶耳”合在一起就是四只“耳朵”。久而久之,“聂耳”这个名字的光芒反倒盖过了他的本名和曾用名,成为他最标志性的符号。“耳”字的造型既是对聂耳本人也是对其才华,同时我想更是对其深远历史影响的铭记。作曲家生前未曾听过《义勇军进行曲》演奏的情形,而今只要提起聂耳、提起中国,每个华人的耳畔、心房都会回响起这明快、昂扬而又雄壮的旋律:
在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的鹄沼海岸,每年的7月17日都会有一支由日本青壮年组成的藤泽市消防音乐队郑重其事地演奏《义勇军进行曲》,为的是纪念在这里不幸溺水去世的中国作曲家聂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曲作者。1935年7月17日,聂耳在鹄沼海岸附近水域游泳时与世长辞,年仅23岁。在中日尚未建交的1954年,藤泽市民就为聂耳修建了纪念碑,此后几经风雨又几经重建、改建。不但如此,如今每个月的第一个周六上午都有不少中日友好人士相约到纪念广场来打扫卫生。八十多年过去了,聂耳已经成为中日民间友好交往的重要纽带。

历史上的云南会馆,聂耳曾短暂居住于此 图片由冯雷提供。
聂耳以音乐为志业,自1931年入行之后他的主要活动都集中在上海,其间曾短暂地北上进京,重返上海之后又选择了东渡日本。北上、东渡的选择与经历是考察聂耳生活、思想轨迹的两个醒目的抓手,因为聂耳两度离沪都是基于对周围环境的考虑以及对理想和出路的寻求。孔子云:“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而聂耳的考虑、寻求莫不与志道、游艺息息相关。对于聂耳来说,志道、游艺又是与救亡、启蒙辩证统一的。所以在北平和东京的这段“双城记”看起来更像是他短暂一生中两段不容忽视的“进行曲”。矢志不渝,北上进京
乘北京地铁二号线到宣武门,西南口出站,沿着宣武门外大街奔南走,没多远在右手边闪出一条胡同,过去这里一直叫鞑子桥胡同,1965年雅化为达智桥胡同。进了胡同第一个丁字路口往南拐便是校场头条。和达智桥胡同的规整、干净相比,校场头条略逊色几分。路西的七号院离巷子口不远,宅门看起来平淡无奇,同资料照片里气派的广亮大门一比真是相形见绌,尤其是门口的两只石鼓和门簪子上“云南会馆”的匾额早已不见踪迹。1932年11月5日,披着这一年的初雪,聂耳在日记里写道:“北平!算是告了一段落吧!二次重来,不知又待何时?”依依不舍之情可见一斑。第二天下午,聂耳辞别才住了三个月的云南会馆,重返上海。
聂耳在北京的经历同他此前在上海的生活是无法割裂开的。从聂耳的“北平日记”来看,他1932年8月10号到了北平,仅住了十天就动了回上海的念头,在随后的几天里这个想法愈发按捺不住,几番下定决心,无论如何要在9月16号回上海去,为此还曾专门到正阳门车站问讯处打听发车时间、票价、行李等。那最后为什么在北平延宕下来,当初又为什么要来北平呢?
聂耳离开上海,最直接的原因是因为他化名“黑天使”写文章批评亦师亦友的黎锦晖,化名被识破之后,聂耳脱离了黎锦晖领导的明月歌剧社另寻出路。有的人认为这种描述实乃是尊者讳,掩盖了聂耳想要在《芭蕉叶上诗》等剧中扮演角色而未得,于是转而挥笔泄愤的隐情。这种说法流布甚广,但显然把聂耳想得太过狭隘和自私,而且也没有把聂耳的思想成长和转折看成是一个完整的链条,自然也就谈不上理解聂耳诸多看似一时冲动的选择。简单来说,聂耳的“上海日记”大致主要有四方面的内容:爱情烦恼、日常练琴、批评剧团以及自遣自励,后三者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在日记里,聂耳很少自暴自弃,他常常显得充满自信,认为自己可以胜任许多工作,包括在电影里扮演一些角色,并且事实上聂耳是有过从影经历的。另一方面他又时常进行自我教育,“不要忘记自己的发展”。但聂耳对明月歌剧社显然不太满意。1931年春,在初识田汉时聂耳便对黎锦晖“某些不健康、不严肃的倾向”表示了不满,在近一年的时间里他在日记中多次写到只是“帮他们工作”“干完这两年再说”“另走他路吧”,在1932年3月聂耳便萌生过去北平考“艺专”的想法。
聂耳对“明月社”的不满有管理、待遇方面的原因,更主要的还有艺术方面的原因。聂耳少年时曾参加过“学生军”,到上海之后常常以“革命新青年”“革命者”自诩,他时常思考“怎样去做革命的音乐”、如何“能够兴奋起、可以鼓动起劳苦大众的情绪”,他当时的朋友中不乏像于立群、贺绿汀、艾思奇、郁达夫、田汉这样的进步文化人,而黎锦晖却恰恰饱受所谓“靡靡之音”的批评。所以聂耳一方面出于上进之心希望扮演角色,另一方面又撰文批评,这其实并不矛盾,都是有思想脉络可循的。并且当时聂耳和周围一些关系密切的朋友之间不时会交换文章甚至是日记,聂耳动笔也并非头脑一热,而是看到好友金焰在《电影时报》上发表了文章而“一时激起我的发表欲,想对他来一个相继的意见”。由此可见,聂耳进剧社、写文章、上北京,这些正如同他成长道路上一系列前后相继的车站一般,并非临时起意。这样似乎就可以更加明确聂耳进京的意图:在思想上追求进步,在艺术上寻求提高,在个人前途上谋求发展。

2019年7月17日,在日本藤泽市聂耳纪念广场上举行的纪念聂耳仪式 图片由冯雷提供。
彷徨、失意、奋起:在北平靠近革命聂耳住进云南会馆的当天就和在北平的朋友们取得了联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抵达北平之后的第三天,聂耳便去拜会了黎锦晖的四弟黎锦舒,两个人谈话多时,黎锦舒还建议聂耳到欧洲去。后来重回上海之后的第二天,聂耳就在曾被他批评过的卜万苍家中遇到了黎锦晖的七弟黎锦光的太太,日记里记载说:“七嫂子好像比以前活泼些,对我很有好感。”由此可见聂耳与黎锦晖及其周围亲友之间未见得已经闹得关系破裂、形同陌路。
中山公园、大栅栏、东安市场、什刹海、北海公园、北京动物园、双清别墅、香山饭店、卧佛寺、碧云寺、清华园、燕园……和今天的游客一样,聂耳也是先到这些地标景点玩了个遍。但他毕竟不是来旅游的,而是带着目标来的。从日记来看,聂耳一方面也希望能进正规大学系统学习,到北京20天后他的日记里便出现了周围朋友们投考学校的内容;但另一方面他在上海养成的自我激励、自我批评的心理又刺激他担心校园生活太过悠闲、使自己“软化下去”。两种心理此消彼长,难以决断。一度下定决心回上海也正是这种犹豫、焦虑心态的体现。读聂耳的日记时常会让我想到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其实聂耳的日记也正是一部更加贴近真实生活的“自叙传”,把20世纪30年代的聂耳同20年代的丁玲、莎菲放在一起,这或许会使人们更容易体会聂耳的烦躁、彷徨、忧虑和希冀,更容易在伟大和年轻之间恰切地想象聂耳。
北平是历史文化名城,经过“文学革命”的洗礼与“革命文学”的筛选,到20世纪30年代北平形成了阵容齐整的“京派”文人圈,他们追求艺术的醇正和恬静,批评低级趣味和商业竞买,特别是后者,正与聂耳相合。在朋友们的建议下,聂耳参加了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的入学考试,但是名落孙山。北平艺院前身为1918年创办的北京美术学校,此后历经变更,1928年改为北平大学艺术学院,1949年撤销。校址原位于西单京畿道,现在似乎已经湮没不存了。在放榜之前,聂耳找到了在东交民巷里栖身的白俄小提琴教师托诺夫,和他学习以期提高琴艺,断断续续持续到10月中旬,因学费难以为继而被迫终止。这些都是聂耳在北平耽搁下来的原因,而此外还有一些原因则是聂耳在日记中未曾多说也不便多说的。
1928年,聂耳在昆明时便秘密加入了共青团,到上海之后对革命文艺则更加关注,甫一住进云南会馆便引起了便衣特务马匡国的注意,此后聂耳在日记里则以“马三哥”代之。值得一提的是,在聂耳入住之前,云南会馆曾经是云南党组织创建过程中最早的基地。五四运动中,云南青年成立了“大同社”,1922年后,大同社成员多数潜入北京,在云南会馆里组织起“新滇社”,在此之后部分新滇社成员秘密入党并回云南创立了党组织。今天在校场头条胡同口的简介里对这段历史也略有提及。
当然同样关注着聂耳的还有地下党组织,特别是“北平左翼戏剧家联盟”,上海方面也给北平剧联的负责人寄来了关于聂耳的介绍信。在北平剧联的吸纳和引领之下,聂耳积极参与了不少进步的文艺活动。在落榜之后,为北平剧联的机关报《戏剧新闻》写稿、参加文艺演出,尤其是作为主要负责人筹建“北平左翼音乐家联盟”成为聂耳在北平的主要活动。特别是在朋友的影响下,聂耳的创作欲再度躁动起来,计划以他“由云南至广、湖的实际生活为取材,写成一篇长篇小说”,并在日记里列了一份大纲。他还把自己和同乡诗人柯仲平做了比较,认为:“说起云南的柯仲平的创作精神,使我觉得自己也可能做出和他差不多的作品,我有的是充分的材料。”只可惜天妒英才,假以时日的话聂耳未尝不会在文艺批评乃至文学创作领域开拓出一片天地来。
北上之行虽然只有区区三个月,但是对聂耳来说却可谓影响深远。直观地来看,离开北平之后,聂耳的日记较之以往稀疏了许多,1933年常常是一连几日都付之阙如,1934年和1935年留日之前各只记了三天。而在音乐创作和著述上,聂耳则迎来一个明显的高峰,特别是在音乐创作方面,日后人们耳熟能详的《开矿歌》《卖报歌》《毕业歌》《梅娘曲》《金蛇狂舞》等全都作于聂耳离开北平之后。显见得聂耳在艺术创作上更加投入了,他甚至觉得“写信比写日记重要”。
更为隐蔽和内在的是,聂耳在思想上更加成熟了,在1932年11月7日离开北平之后,1933年初由赵铭彝、田汉做介绍人,夏衍监誓,聂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更加深入地参加到“左联”领导下的文艺工作中来,这或许才是聂耳转变的内在驱动力。如果说是摩登的上海为聂耳提供了最华丽的舞台的话,那质朴的北平给予聂耳的“挫折教育”则助力这位天才的音乐家拉开了人生舞台上那掩饰了许多未知与可能的神秘大幕。

《义勇军进行曲》的影写谱,原载《电通》画报1935年6月1日第2期 图片由冯雷提供。
东渡赴日:求学周恩来曾就读的学校聂耳是因为躲避抓捕而于匆促之间赴日的,但赴日其实也一直是聂耳的梦想。在云南读书时,聂耳便选修过日语,在北平落榜之后前途渺茫之际聂耳也曾憧憬过到日本去,但因为没有钱而打消了念头。除却个人方面的原因之外,到日本去还与晚清以来的诸多社会因素有关,最主要的是甲午一战带给中国的莫大刺激,举国上下皆谓守旧不变终非长计。当然清政府也有许多顾虑,唯恐过分摄取西学而影响自身政体的安危,较之欧美,“地属同洲政体民情最为相近”的日本就成为最适宜的对象,因之制定了一系列留学政策。张之洞在《劝学篇》里辩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各种西学书之要者,日本皆以译之,我取径于东洋,力省效速”。梁启超也认为日文音少、无棘刺扞格之音、文法疏阔、名物象事多与中土相同、汉文居十六七,所以学习日文要更为容易。此外,留学日本“文同、地近、费省”也是颇为实际的因素。在这些之外,也不能忽视日本官绅在中国的热心延揽,只是在“维持东亚经纶之大策”的包装之下掩藏着的却是文化殖民的祸心。在多重因素的合力之下,虽然“读的是西洋书,受的是东洋气”,但赴日留学者仍然浩浩荡荡,最多时一年有八千余人,在聂耳赴日的1935年还出现了约6500人的小高峰。日本方面也相应设立了许多为中国留学生而办的学校,例如培养了一众日后知名人物的成城学校、弘文学院、振武学校以及聂耳就读的“东亚高等预备学校”。
比起当初到北平时先是游玩了一番,聂耳抵达东京的当天就到“东亚”听了两个小时的日语课,第二天就报了名入学。其实当看到聂耳是在“东亚”补习日语时,我不禁在心里暗暗画了个惊叹号,因为1936年萧红到东京后也是在这个学校上课,略长半岁多的萧红还要管聂耳喊一声“学长”。这样一来,这个东亚学校自然就成为不得不去看一看的所在。
经查,东亚学校后来毁于地震,原址已经改为“全爱公园”,位于东京都千代田区神田神保町二丁目,离东京大学并不太远,导航显示步行二十来分钟就能走到。东京的街道比起北京要狭窄得多,尤其是导航规划的步行优化路线,马路更显逼仄。在异国他乡苦心孤诣地寻访先辈同胞的足迹则更有一番难以道尽的感受。几番曲曲折折之后,全爱公园终于闪现出来。名曰公园,实际上非常袖珍,一个喷泉、两个花坛、几棵树木而已。花坛里竖着一碑、一牌。石碑上端醒目地刻着“周恩来曾在此求学”;下端则表明这里便是“东亚高等预备学校遗迹”。旁边的牌子上用日汉双语简要介绍了“日中两国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东亚学校读书的经过,落款是“千代田区日中友好协会”。原来周恩来、聂耳、萧红都曾在这里学习过。我忽而想到那难以道尽的感受中或许包含着“抗拒遗忘”之意。
除了东亚学校之外,聂耳还曾到“日比谷公会堂”“东宝剧场”“九段军人会馆”“新宿第一剧场”等地观摩过许多文艺演出,这几处相距都不太远,我也都一一专门去找过,有的仍然耸立在街头,有的则已经毁弃并随着时间渐渐被人淡忘了。

1934年夏,聂耳(左)与田汉在上海合影 图片由冯雷提供。
抗拒遗忘:异国他乡的纪念提起聂耳,人们最直接想到的恐怕便是《义勇军进行曲》,鲜为人知的是,《义勇军进行曲》是聂耳在东京修改定稿的。当时地下党领导下的“电通影片公司”筹拍新片《凤凰的再生》,由田汉编剧。但田汉刚写出一个故事梗概和主题歌歌词便被捕入狱了,夏衍继续把故事梗概写成电影文学剧本,并改名为《风云儿女》。行将避难的聂耳得知消息后主动请缨为主题歌作曲,他在上海完成初稿,抵达东京之后加工修改,寄回国内。田汉后来听到这支曲子,盛赞聂耳的作曲“爽朗明快,善于处理在别人很不易驾驭的词句,这歌词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是被认为很不容易驾驭的,而他处理得很自然有力。”在谱曲之外,聂耳还结合音乐旋律对田汉的原作做了一些调整,尤其是在“我们万众一心”之前三呼原稿开篇的“起来”,强化了步步高涨的气势。
然后在历史的氧化作用下,有些细节却渐渐涣漫不清了。有不少文章包括田汉本人都引用了孙师毅的回忆,说《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是写在一张包香烟的锡纸的衬纸上。而夏衍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纠正说田汉的《入狱》才写在这种衬纸上,是田汉记错了。田汉的剧本梗概“写在旧式十行红格纸上,十余页。《义勇军进行曲》这首主题歌,写在原稿的最后一页,因在孙师毅同志书桌上搁置了一个星期,所以最后一页被茶水濡湿,有几个字看不清楚。”如果说这种错讹与当时动荡的社会环境和当事人的记忆偏差有关,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另有些明显的错误则实在令人费解。有不少资料里都把聂耳和同乡好友廖伯民的合影错当作是聂耳与田汉的合影,以讹传讹。事实上,田汉留下来的照片非常多,而且田、廖二人面貌差异明显,稍加辨认即当错不至此。我在东京有幸遇到田汉的后人,经过询问确认聂廖合影中的不是田汉。
从日记可以看得出,聂耳到日本之后时间上利用得非常紧凑,日记中也时常蹦出几个日文单词来。聂耳制定了四个“三月计划”,到日本两个多月的时候,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愉快地通报自己以学习日语为主的第一个“三月计划”“仅仅两月功夫便全部实现”。在东京,聂耳在音乐、戏剧和电影方面都做了不少深入的调查和总结,从他遗留的著述可以看出,聂耳在坚持左翼革命文艺立场的同时,汲汲于了解国外同行的技艺创新、潮流动向,这和他在国内时的思想发展是一脉相承的。如果不是天不假年,那么这段海外之旅完全有可能成为聂耳在艺术上新的酝酿期和孵化期。按照原计划,一年之后聂耳还打算到苏联、欧洲去。但是到日本才刚刚三个月,聂耳却因为一场意外在日本成为永远的不归之客。
说实话,“不归之客”这个词我还是在藤泽的聂耳纪念广场的碑文中第一次见到。1950年,日本马克思主义者福本和夫从英文版的《人民中国》上看到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以及聂耳的报道,他请藤泽市议员叶山冬子翻译了这篇报道和《义勇军进行曲》歌词。聂耳及其在藤泽市的活动于当地得以传播开来。同年11月,“聂耳纪念之夜”活动在藤泽市举行,《义勇军进行曲》在聂耳殒没的地方奏响。1952年福本和夫首倡为聂耳竖立纪念碑,1954年纪念碑落成。从1896年清政府选派首批13名留日生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四十年间负笈东游者至少在95000人,而日本为之塑像立碑者却屈指可数,聂耳正是其中之一。然而在1958年“狩野川”台风中纪念碑却被巨浪卷走了。藤泽市民于1963年成立了聂耳纪念碑保存会,重新筹建纪念碑。纪念碑原来位于引地川河口,可用之地狭窄,1965年新纪念碑在现在的位置落成,此后历经翻修、扩建,形成了现在聂耳纪念广场的形制和规模。
广场背倚相模湾,不远处就是著名的景点江之岛,不少人在近海处冲浪、嬉戏,还有许多人在广场周围的沙滩上烧烤、打球,乌鸦和老鹰自由地飞翔在天空上,周围的气氛非常轻松、惬意。现如今,广场上共有六块各具来历的碑铭,其中一块是由1986年时任藤泽市长的叶山峻题写的《聂耳纪念碑的由来》。可能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位叶山峻的母亲就是当年翻译《义勇军进行曲》的叶山冬子。两代人前仆后继、薪火相传,这使得聂耳纪念碑更具纽带意义,不但连接着中日两国,同时也连接着日本国内的友好人士。
在纪念广场中央竖立着一座造型奇特的祭台,仔细一看,祭台的平面乃是一个“耳”字的造型。在学艺的过程中,人们发现聂耳别具耳聪,听得出、记得住、弹得来,所以戏称他“耳朵”。在当时“聂”字用繁体写作“聶”,“聶耳”合在一起就是四只“耳朵”。久而久之,“聂耳”这个名字的光芒反倒盖过了他的本名和曾用名,成为他最标志性的符号。“耳”字的造型既是对聂耳本人也是对其才华,同时我想更是对其深远历史影响的铭记。作曲家生前未曾听过《义勇军进行曲》演奏的情形,而今只要提起聂耳、提起中国,每个华人的耳畔、心房都会回响起这明快、昂扬而又雄壮的旋律: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光明日报》( 2019年11月29日 13版)本文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责任编辑:殷思佳
免责声明:
1、凡本网注明“来源:***(非中国警营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的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2、如因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需要同本网联系的,请在30日内进行。
相关阅读
- 2023-05-15让经典旋律成为与世界对话的语言(创作者谈)
- 2023-05-12纽约中小学生探秘百老汇 感受音乐剧舞台魅力
- 2023-05-11首届天津音乐节正式开票
- 2023-05-10民族器乐童话剧《神笔马良》在京首演
- 2023-05-09倾听普洱澜沧天籁:大师经典作品爵士音乐会将于5月14日在上海开演
头条图文
热点推荐
精选图文
阅读排行榜
品牌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