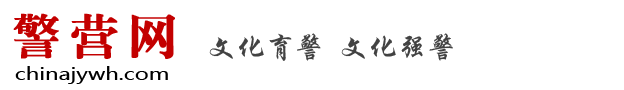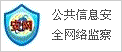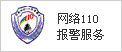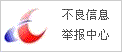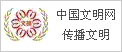在科幻这件事上,戏剧赢了影视
2020-11-27 10:44:10
来源:北京青年报
责任编辑:周健森
过去的一个月,我活得很科幻。
因为参与了2020中国科幻大会第二届科幻影视创投会的评审工作,我在一个月的时间里阅读了126个科幻电影项目的资料。在此期间,刚好借中间剧场举办“科技艺术节”之机,又观看了《银河怒》和《一亿亿亿字节人生》这两部新近创排的科幻题材戏剧作品,并且重温了《好几个》《狗还在叫》《静态人像》等带有科幻元素的舞台旧作,可以说每天都沉浸在科幻的氛围里。 电影与戏剧,原本分属不同的艺术领域,但是放在科幻的语境之下,二者似乎还是可以拿来相提并论的。就我个人而言,将科幻电影与科幻戏剧相比较,比拼的一定不是投资成本、视觉效果或票房收入,而是创作者对未来的想象力,对人类命运的前瞻眼光,以及对当下科技环境的批判与思考。此番比较的结果,是我有一天在微信朋友圈里撂下一句判断:“在科幻这件事上,戏剧赢了影视。”
电影与戏剧,原本分属不同的艺术领域,但是放在科幻的语境之下,二者似乎还是可以拿来相提并论的。就我个人而言,将科幻电影与科幻戏剧相比较,比拼的一定不是投资成本、视觉效果或票房收入,而是创作者对未来的想象力,对人类命运的前瞻眼光,以及对当下科技环境的批判与思考。此番比较的结果,是我有一天在微信朋友圈里撂下一句判断:“在科幻这件事上,戏剧赢了影视。”
电影篇:科幻少了“科”,幻想变妄想
中国科幻大会的科幻影视创投会,堪称国内科幻界专业度最高的顶级影视创投活动。不过坦率地讲,在短时间内密集阅读大量剧本,并不是一件愉悦的事情。抛开创作者在剧作能力上的优劣不谈,真正让我介意的是,这些科幻影视项目在核心创意和题材选择上存在高度重合的问题,以至于当我阅读这些剧本时,一度以为自己陷入了死循环的怪圈之中。
为了证实这种印象不是错觉,我特意在事后对这126个项目的题材进行了一番统计:126个项目中,关于人工智能的有25个,涉及记忆移植或存储的有16个,讲述“世界虚拟论”的有14个,另外还有11个是关于平行时空或多维宇宙的。如果说创作者在热门题材上“撞车”属于正常现象,那么这些同题材科幻剧本中频繁出现的相似情节和叙事套路,就真的有些说不过去了。
比如,关于人工智能的项目,里面的人工智能无论是有实体的机器人还是一个虚无缥缈的程序,只要有了自主意识,十有八九都怀着谋害人类、篡位夺权的野心。再比如被平行时空困扰着的那些主人公,他们只要掉入无限循环的陷阱,并且遇到了另一个自己之后,一言不发便上演“大逃杀”,连个彼此商量的余地都没有,好像你死我活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其实我们大可不必为这些创作者遮掩,他们的所谓原创剧本,其实许多都是拿近年来国外经典或爆款作品作为模仿的“对标作品”。涉及人工智能题材的故事,大多看着像《黑镜》的某一集;讲述平行时空大逃杀,无非是把《恐怖游轮》或《彗星来的那一夜》改了个场景;跨时空接触,一律照抄《黑洞频率》《信号》的设定;至于宇宙深空冒险,要么看着像《星际穿越》,要么就是学《太空旅客》。
这不是科幻影视独有的问题,而几乎是我们当下商业电影创作领域的通病。 然而有意思的是,相当多比例的创作者不约而同地选择以“暗黑向”的国外科幻影视作品作为模仿对象。在我所读的大量剧本中,充斥着末世的荒凉、灾难的无序、死亡的威胁、血腥的杀戮。科幻作为自诞生以来便显现出强烈警世意义的叙事类型,许多经典作品都会传递出明确的危机感,但今天的创作者如此一致地表达出对未来的悲观态度,倒似乎是有种集体无意识的幽灵在作祟。
然而有意思的是,相当多比例的创作者不约而同地选择以“暗黑向”的国外科幻影视作品作为模仿对象。在我所读的大量剧本中,充斥着末世的荒凉、灾难的无序、死亡的威胁、血腥的杀戮。科幻作为自诞生以来便显现出强烈警世意义的叙事类型,许多经典作品都会传递出明确的危机感,但今天的创作者如此一致地表达出对未来的悲观态度,倒似乎是有种集体无意识的幽灵在作祟。
还是以人工智能题材为例,“AI威胁论”确实是近年来科幻影视中经常探讨的议题。如近年来热播的《西部世界》《异星灾变》《智能逆袭》等美剧,都是建立在这个主题上生发出来的优质作品。但不可忽略的是,类似于《她》《我的机器人女友》《安堂机器人》等作品所畅想的“人机和谐共处”的未来图景,却似乎被许多国内的创作者集体无视了。
也许这些创作者觉得人机对抗才有戏剧冲突,剧情“烧脑”才是王道,但事实上,如果他们认真阅读科学家、工程师或专业学者的著作就会发现,“AI威胁论”更多呈现为流行文化取悦大众的噱头,对“人机协作”审慎乐观的积极态度,才是更为现实的主流观念。比如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戴维·明德尔在《智能机器的未来》一书中,就将其描述为“一个美丽的科技新世界”。
另外,即使是对人工智能未来潜在风险发出预警信号的人文学者们,也更多是在伦理、哲学、政治甚至宗教等领域进行严肃探讨,而不是简单粗暴地宣扬所谓“人机二元对立”。预言了“数据主义”未来图景的网红学者尤瓦尔·赫拉利,就曾在其《未来简史》一书中揶揄好莱坞编剧:“你还真以为,如果全知的超级计算机或外星人都要征服整个星系了,还会被(人类)激素暴发这种小事糊弄?”
当然,我们没必要苛求所有科幻影视创作者都能像克里斯托弗·诺兰那样,为了拍摄《星际穿越》去研究黑洞的形状,可是如果挂着科幻的幌子却连自己所写题材的基础科学原理都不去了解,则未免有些说不过去。要知道,即使是“世界虚拟论”这种带有高度假说色彩的猜想,其提出者尼克·波斯特罗姆本人也是兼具技术人员头衔的哲学家,而他的理论推导过程是相当科学且缜密的。
反观我们的一些科幻影视创作者,把科学当成了可有可无的工具。如果情节漏洞百出,那就祭出量子力学;如果深空旅行枯燥无趣,那就随便在太阳系开个黑洞;可是如果科学妨碍了他们所谓的“爽感”,那就赶紧丢到一边去。当我读剧本时看到一个主人公为了破解平行时空之谜,花费十几年翻烂了各种天体物理学书籍,台词里却说不出一句像样的理论时,很不厚道地发出了笑声。

如果科幻丧失了起码的科学基础,仅存的幻想与妄想还有什么分别?这是我在本届创投活动结束之后仍然摆脱不掉的疑问。过去数年来,许多中国科幻创作者和影视工作者都在致力于打造属于中国的科幻影视航母。去年,《流浪地球》成功开启了“科幻元年”,让人们看到了国产科幻电影的希望,但随后长久的沉寂又让人担心这样的热情可能转瞬便会熄灭。
我想,中国科幻大会设立影视创投会的意义,并非在于发掘下一个爆款大片,而是持续地将更多优质且多元的作品从创作端输送到市场。这意味着我们的科幻影视事业不应当依赖“复制粘贴”实现所谓的规模化,而是去持续不断地寻找那些真诚的创作者,帮助他们实现用影像手段讲述科幻故事的梦想。我所说的真诚,首先是创作意识上的真诚,同时还应当包括对观众和市场的真诚。
今天当我们讨论中国科幻影视时,可能已不必再把重工业或市场承载力当作话题的焦点,而是要切实思考“中国”的分量和“科幻”的真意。就我个人的意见来说,中国科幻一定不能是好莱坞B级片的移植或本土化改造,更不应该成为某个亚文化圈子的自嗨游戏,回归到对科学精神和人文主义的信仰,或许才是中国式科幻不同于好莱坞电影的一条自选道路。
戏剧篇:未来这么近,现实那么远
不得不说,当我从影视剧本中抽离出来,回到剧场观看《银河怒》和《一亿亿亿字节人生》这两部新近创排的话剧作品时,竟然有了一种劫后余生的喜悦感。不同于科幻影视中常见的宏大视效场面,也没有商业类型片中套路化的一波三折,这两部话剧作品给人的直观印象是朴素甚至简陋的,但有限的条件非但没有束缚创作者的观念,反而激发了他们的想象力,甚至让人觉得这才是科幻该有的味道。 因为有歌德学院参与今年的科技艺术节,这两部话剧的编剧都是德国戏剧工作者,而舞台呈现方面则全部交由中国的戏剧工作者来完成。特别难得的是,此次跨地域合作并没有出现过往一些作品中尴尬的文化误读问题,反而是国内的创作者在对本地化改编中冒出了不少令人惊喜的念头。我想,这可能得益于作为全球性议题的科幻或科技主题,为两国的创作者提供了高度相似的共同语境。
因为有歌德学院参与今年的科技艺术节,这两部话剧的编剧都是德国戏剧工作者,而舞台呈现方面则全部交由中国的戏剧工作者来完成。特别难得的是,此次跨地域合作并没有出现过往一些作品中尴尬的文化误读问题,反而是国内的创作者在对本地化改编中冒出了不少令人惊喜的念头。我想,这可能得益于作为全球性议题的科幻或科技主题,为两国的创作者提供了高度相似的共同语境。
《银河怒》和《一亿亿亿字节人生》都不是由单一完整故事构成的作品,而是不约而同地用情节拼贴的方式完成。但是这非但没有给观众造成理解上的障碍,恰恰相反,因为创作者撷取的素材都来自当下的现实世界,而非虚无缥缈的未来,因此无论是细节的高度真实性,还是对人们现实困境的把握,更令人有了强烈的共鸣感。
“一亿亿亿字节”听上去是个夸张到令人几乎无感的数字,但是剧作者奥利维亚·文策尔告诉我们,按照现在网络数据量每年40%的增长速度,一亿亿亿字节将是十年之后的人类数据量总和。这是一个具体到人人可期的时间节点,我们接下来还将被告知,这个数字意味着我们从出生到死亡的全部人生,都能以视频化的形式被记录并保存下来,或用剧中人的话来说,“你的小视频活得比你久。” 从这个概念被灌输到观众的意识中起,曾经的“数字化生存”陡然上升为一个哲学命题。剧作者并没有拘泥于去复述我们现实中的细碎烦恼,诸如隐私权、网络暴力、社交困境等老生常谈的问题,而是将剧中的主人公扔进试验箱中去直面未来的生活。他也并不急于做出是非善恶的判断,而是理性地抛出一个又一个问题,并最终让我们意识到:所有这些看似琐碎的事情都是有关联的,对吧?
从这个概念被灌输到观众的意识中起,曾经的“数字化生存”陡然上升为一个哲学命题。剧作者并没有拘泥于去复述我们现实中的细碎烦恼,诸如隐私权、网络暴力、社交困境等老生常谈的问题,而是将剧中的主人公扔进试验箱中去直面未来的生活。他也并不急于做出是非善恶的判断,而是理性地抛出一个又一个问题,并最终让我们意识到:所有这些看似琐碎的事情都是有关联的,对吧?
不同于《一亿亿亿字节人生》十分贴合现实的近未来设定,《银河怒》用改变我们观察世界的角度来制造陌生化效果,从而将观众从固有的刻板思维中抽离了出来。韩裔德籍编剧朴本幻想出了一个外星生物学家,在对地球进行了一番长期观察,目睹了诸多令他无法理解的“荒诞行为大赏”之后,他对人类发出了一句咒骂式的警告:你们这么愚蠢,这么混球,然后又这么可爱。
朴本的创作显然得益于他的移民身份,这使他可以体会到人类交流的无望与艰难。在《银河怒》中,他特意选取了东西方左右地球命运的人物作为供人们观察的主人公。颇为讽刺的是,当我们借由外星人的视角近距离观察他们的时候,这些手握权力的角色看上去并没有那么邪恶,他们单纯可爱,甚至善良,他们因为不被他人理解而感到沮丧,但他们似乎也并不准备理解他人,因而更加绝望。 《银河怒》这部作品让我感到颇受启发的地方在于,创作者并没有营造什么光怪陆离的视觉奇景,而仅仅是调整了观众的视角,就足以制造出颠覆想象和撼动三观的效果,这种智慧本身才是艺术家所应具备的天赋和想象力,也是科幻作品真正令人着迷的本质所在。反观影视行业一味追求工业视效的科幻题材创作者,或许真的可以学一学这种更为高级也更为纯粹的创作思路。
《银河怒》这部作品让我感到颇受启发的地方在于,创作者并没有营造什么光怪陆离的视觉奇景,而仅仅是调整了观众的视角,就足以制造出颠覆想象和撼动三观的效果,这种智慧本身才是艺术家所应具备的天赋和想象力,也是科幻作品真正令人着迷的本质所在。反观影视行业一味追求工业视效的科幻题材创作者,或许真的可以学一学这种更为高级也更为纯粹的创作思路。
这种四两拨千斤的智慧,也在舞台呈现上被两位初出茅庐的中国导演发挥得淋漓尽致。《银河怒》的导演许鸿昌用乐高玩具加现场拍摄的形式,准确地传递出了剧本中的戏谑意味和游戏感;《一亿亿亿字节人生》的导演王光皓则借用廉价的塑料薄膜,带领观众沉浸到了被隔离的屏幕人生之中。我甚至觉得,正是捉襟见肘的投入本身,逼得青年导演们使出了奇招,同时也成就了作品的轻盈质感。
我特别喜欢王光皓对《一亿亿亿字节人生》剧本的二度创作思考,他最终从数字的洪流中解救出了即将被吞没的主人公,使得整个故事有了一个青春偶像剧般的乐观且欢快的结局。但是在一个经过特殊设计的谢幕环节中,我突然发现依然有一道硕大无边的“屏幕”将我们与主人公隔绝了开来。就在那个瞬间,角色和观众的位置发生了颠倒,而我们离他们看似这么近,其实那么远。(周健森)
因为参与了2020中国科幻大会第二届科幻影视创投会的评审工作,我在一个月的时间里阅读了126个科幻电影项目的资料。在此期间,刚好借中间剧场举办“科技艺术节”之机,又观看了《银河怒》和《一亿亿亿字节人生》这两部新近创排的科幻题材戏剧作品,并且重温了《好几个》《狗还在叫》《静态人像》等带有科幻元素的舞台旧作,可以说每天都沉浸在科幻的氛围里。

电影篇:科幻少了“科”,幻想变妄想
中国科幻大会的科幻影视创投会,堪称国内科幻界专业度最高的顶级影视创投活动。不过坦率地讲,在短时间内密集阅读大量剧本,并不是一件愉悦的事情。抛开创作者在剧作能力上的优劣不谈,真正让我介意的是,这些科幻影视项目在核心创意和题材选择上存在高度重合的问题,以至于当我阅读这些剧本时,一度以为自己陷入了死循环的怪圈之中。
为了证实这种印象不是错觉,我特意在事后对这126个项目的题材进行了一番统计:126个项目中,关于人工智能的有25个,涉及记忆移植或存储的有16个,讲述“世界虚拟论”的有14个,另外还有11个是关于平行时空或多维宇宙的。如果说创作者在热门题材上“撞车”属于正常现象,那么这些同题材科幻剧本中频繁出现的相似情节和叙事套路,就真的有些说不过去了。
比如,关于人工智能的项目,里面的人工智能无论是有实体的机器人还是一个虚无缥缈的程序,只要有了自主意识,十有八九都怀着谋害人类、篡位夺权的野心。再比如被平行时空困扰着的那些主人公,他们只要掉入无限循环的陷阱,并且遇到了另一个自己之后,一言不发便上演“大逃杀”,连个彼此商量的余地都没有,好像你死我活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其实我们大可不必为这些创作者遮掩,他们的所谓原创剧本,其实许多都是拿近年来国外经典或爆款作品作为模仿的“对标作品”。涉及人工智能题材的故事,大多看着像《黑镜》的某一集;讲述平行时空大逃杀,无非是把《恐怖游轮》或《彗星来的那一夜》改了个场景;跨时空接触,一律照抄《黑洞频率》《信号》的设定;至于宇宙深空冒险,要么看着像《星际穿越》,要么就是学《太空旅客》。
这不是科幻影视独有的问题,而几乎是我们当下商业电影创作领域的通病。

还是以人工智能题材为例,“AI威胁论”确实是近年来科幻影视中经常探讨的议题。如近年来热播的《西部世界》《异星灾变》《智能逆袭》等美剧,都是建立在这个主题上生发出来的优质作品。但不可忽略的是,类似于《她》《我的机器人女友》《安堂机器人》等作品所畅想的“人机和谐共处”的未来图景,却似乎被许多国内的创作者集体无视了。
也许这些创作者觉得人机对抗才有戏剧冲突,剧情“烧脑”才是王道,但事实上,如果他们认真阅读科学家、工程师或专业学者的著作就会发现,“AI威胁论”更多呈现为流行文化取悦大众的噱头,对“人机协作”审慎乐观的积极态度,才是更为现实的主流观念。比如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戴维·明德尔在《智能机器的未来》一书中,就将其描述为“一个美丽的科技新世界”。
另外,即使是对人工智能未来潜在风险发出预警信号的人文学者们,也更多是在伦理、哲学、政治甚至宗教等领域进行严肃探讨,而不是简单粗暴地宣扬所谓“人机二元对立”。预言了“数据主义”未来图景的网红学者尤瓦尔·赫拉利,就曾在其《未来简史》一书中揶揄好莱坞编剧:“你还真以为,如果全知的超级计算机或外星人都要征服整个星系了,还会被(人类)激素暴发这种小事糊弄?”
当然,我们没必要苛求所有科幻影视创作者都能像克里斯托弗·诺兰那样,为了拍摄《星际穿越》去研究黑洞的形状,可是如果挂着科幻的幌子却连自己所写题材的基础科学原理都不去了解,则未免有些说不过去。要知道,即使是“世界虚拟论”这种带有高度假说色彩的猜想,其提出者尼克·波斯特罗姆本人也是兼具技术人员头衔的哲学家,而他的理论推导过程是相当科学且缜密的。
反观我们的一些科幻影视创作者,把科学当成了可有可无的工具。如果情节漏洞百出,那就祭出量子力学;如果深空旅行枯燥无趣,那就随便在太阳系开个黑洞;可是如果科学妨碍了他们所谓的“爽感”,那就赶紧丢到一边去。当我读剧本时看到一个主人公为了破解平行时空之谜,花费十几年翻烂了各种天体物理学书籍,台词里却说不出一句像样的理论时,很不厚道地发出了笑声。

如果科幻丧失了起码的科学基础,仅存的幻想与妄想还有什么分别?这是我在本届创投活动结束之后仍然摆脱不掉的疑问。过去数年来,许多中国科幻创作者和影视工作者都在致力于打造属于中国的科幻影视航母。去年,《流浪地球》成功开启了“科幻元年”,让人们看到了国产科幻电影的希望,但随后长久的沉寂又让人担心这样的热情可能转瞬便会熄灭。
我想,中国科幻大会设立影视创投会的意义,并非在于发掘下一个爆款大片,而是持续地将更多优质且多元的作品从创作端输送到市场。这意味着我们的科幻影视事业不应当依赖“复制粘贴”实现所谓的规模化,而是去持续不断地寻找那些真诚的创作者,帮助他们实现用影像手段讲述科幻故事的梦想。我所说的真诚,首先是创作意识上的真诚,同时还应当包括对观众和市场的真诚。
今天当我们讨论中国科幻影视时,可能已不必再把重工业或市场承载力当作话题的焦点,而是要切实思考“中国”的分量和“科幻”的真意。就我个人的意见来说,中国科幻一定不能是好莱坞B级片的移植或本土化改造,更不应该成为某个亚文化圈子的自嗨游戏,回归到对科学精神和人文主义的信仰,或许才是中国式科幻不同于好莱坞电影的一条自选道路。
戏剧篇:未来这么近,现实那么远
不得不说,当我从影视剧本中抽离出来,回到剧场观看《银河怒》和《一亿亿亿字节人生》这两部新近创排的话剧作品时,竟然有了一种劫后余生的喜悦感。不同于科幻影视中常见的宏大视效场面,也没有商业类型片中套路化的一波三折,这两部话剧作品给人的直观印象是朴素甚至简陋的,但有限的条件非但没有束缚创作者的观念,反而激发了他们的想象力,甚至让人觉得这才是科幻该有的味道。

《银河怒》和《一亿亿亿字节人生》都不是由单一完整故事构成的作品,而是不约而同地用情节拼贴的方式完成。但是这非但没有给观众造成理解上的障碍,恰恰相反,因为创作者撷取的素材都来自当下的现实世界,而非虚无缥缈的未来,因此无论是细节的高度真实性,还是对人们现实困境的把握,更令人有了强烈的共鸣感。
“一亿亿亿字节”听上去是个夸张到令人几乎无感的数字,但是剧作者奥利维亚·文策尔告诉我们,按照现在网络数据量每年40%的增长速度,一亿亿亿字节将是十年之后的人类数据量总和。这是一个具体到人人可期的时间节点,我们接下来还将被告知,这个数字意味着我们从出生到死亡的全部人生,都能以视频化的形式被记录并保存下来,或用剧中人的话来说,“你的小视频活得比你久。”

不同于《一亿亿亿字节人生》十分贴合现实的近未来设定,《银河怒》用改变我们观察世界的角度来制造陌生化效果,从而将观众从固有的刻板思维中抽离了出来。韩裔德籍编剧朴本幻想出了一个外星生物学家,在对地球进行了一番长期观察,目睹了诸多令他无法理解的“荒诞行为大赏”之后,他对人类发出了一句咒骂式的警告:你们这么愚蠢,这么混球,然后又这么可爱。
朴本的创作显然得益于他的移民身份,这使他可以体会到人类交流的无望与艰难。在《银河怒》中,他特意选取了东西方左右地球命运的人物作为供人们观察的主人公。颇为讽刺的是,当我们借由外星人的视角近距离观察他们的时候,这些手握权力的角色看上去并没有那么邪恶,他们单纯可爱,甚至善良,他们因为不被他人理解而感到沮丧,但他们似乎也并不准备理解他人,因而更加绝望。

这种四两拨千斤的智慧,也在舞台呈现上被两位初出茅庐的中国导演发挥得淋漓尽致。《银河怒》的导演许鸿昌用乐高玩具加现场拍摄的形式,准确地传递出了剧本中的戏谑意味和游戏感;《一亿亿亿字节人生》的导演王光皓则借用廉价的塑料薄膜,带领观众沉浸到了被隔离的屏幕人生之中。我甚至觉得,正是捉襟见肘的投入本身,逼得青年导演们使出了奇招,同时也成就了作品的轻盈质感。
我特别喜欢王光皓对《一亿亿亿字节人生》剧本的二度创作思考,他最终从数字的洪流中解救出了即将被吞没的主人公,使得整个故事有了一个青春偶像剧般的乐观且欢快的结局。但是在一个经过特殊设计的谢幕环节中,我突然发现依然有一道硕大无边的“屏幕”将我们与主人公隔绝了开来。就在那个瞬间,角色和观众的位置发生了颠倒,而我们离他们看似这么近,其实那么远。(周健森)
本文来源:北京青年报责任编辑:周健森
免责声明:
1、凡本网注明“来源:***(非中国警营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的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2、如因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需要同本网联系的,请在30日内进行。
相关阅读
- 2023-05-15电影《京门烽火》定档6月9日
- 2023-05-12大女主时代来了,先锋国剧《外婆的新世界》收获口碑和热度双高
- 2023-05-11《纵然》官宣开机 重磅打造跨越时空的勇敢奔赴
- 2023-05-10《长安三万里》发布定档预告 壮美大唐山河辽阔
- 2023-05-09《闪电侠》国内首波口碑出炉 全片高能掀好评狂潮
头条图文
热点推荐
精选图文
阅读排行榜
品牌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