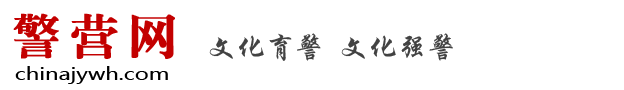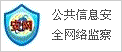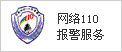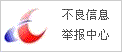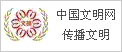当电影成为支点,能否撬动地球
2019-12-16 10:34:18
来源:解放日报
责任编辑:庄加逊
作者:庄加逊
《返归未来》是电影学者戴锦华和王炎围绕电影议题所做的七次深度对谈,时间跨度长达六年。
通过鲜活犀利的思想碰撞,二人将个体记忆与银幕现实置于20世纪动荡多变的历史长流中,向读者揭示出作为特殊叙述文本的电影在“书写”与“呈现”的过程中带来的谜题、反思以及挑战。
专栏结集,尤其是对话体裁,易显得零散,需要调动读者更多的知识及经验储备才能产生代入感。但这本小书读来实在叫人痛快,爱影人心中的“戴爷”延续了她一贯的精准毒辣,在与王炎的文字交锋中重新发现了电影,做了别样的发问。
电影的要害,要害的电影
全书的一体成型归功于精彩的编辑,但更为要紧的核心是对电影惯性思维的打破。
人们常说电影是20世纪最伟大的艺术,“艺术”二字的强大光环无疑掩盖了它区别于其他传统人文艺术的两个维度,恐怕也是电影之所以成为电影的构成基因:政治性与科技性。
当然,电影可以拿来像绘画、音乐一般分析其创作手法、艺术风格,我们看过太多诸如此类的谈论电影艺术的书,无须赘述。事实上,在那篇沾满了前人唾沫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中,本雅明就触及了关窍,“人们耗费了不少精力钻牛角尖似的争论摄影到底算不算一门艺术,却没有先问问这项发明是否改变了艺术的普遍特性;而电影理论家也犯下了同样的错误,他们还在努力想让影像更接近于艺术。但这根本不是电影的核心”,“电影这种优越性有助于艺术与科学的互相融合,而这正是电影最重要的地方。当我们观察一个行为与特定的情况配合完美时(比如人体的肌肉运作),我们一点也不知其中的契合是属于艺术表现还是适于科学方面的探索。科学与艺术迄今往往各行其道,可是有了电影,我们可以说摄影的艺术发展与科学探索已结合为一体,这是电影的一大革命性功能”。
再往外延伸一些,政治与艺术品的展览价值有着极为密切、纠缠的关联,当科技、政治、展演三者合一,身为媒介的电影就此成为一个支点,甚至可以撬动整个地球。
看电影的人陷溺在“艺术与故事”中,忘记了从来没有一种艺术如此密切地仰仗科技,从来没有一种艺术可以如此真切地将世界与历史摆在你面前,也能将幻象变得真实,乃至成为改变你自身行为模式、操控历史与政治的书写。
基于这个角度,《返归未来》是第一次集中的、极具爆发力的关于电影政治内涵及科技性特质的聚焦,它告诉读者,我们关于电影的思考不该停留在感官的艺术呈现层次,那是很单薄的视觉误解。
从社会而来,反哺人心
戴锦华拿一个文字游戏比拟了银幕的“二律悖反”:
游戏的对象是“屏蔽”一词。我们在这个词组间加一道斜杠,变成“屏/蔽”。屏本意是遮挡与阻断,但在今日的语言系统中,它更多地对应英文中的screen——银屏、屏幕、视屏,“屏”意味着可见与看见。在电影理论中,电影银幕经常被转喻为窗、框中画,抑或是镜子。当我们着魔般地凝视着屏幕,似乎从无数扇窗口望去:我们看见,我们获知,我们发现。于是,我们忽略了甚至遗忘了屏之本意。每个视窗都同时是一面屏;每一个(屏)显都同时是一次(遮)蔽;我们在看见的同时不见。
有了这个立足点,再来看电影,一切变得意味深长:历史是权力的书写、胜利者的清单,同时也可以是个体记忆对既有历史的质疑与重写;好莱坞电影工业展现了美国政坛风雨,同时也反过来再造美国政界的姿态;究竟是恐怖主义促发了反恐题材电影的兴盛,还是电影创造了恐怖主义的想象;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完成以及数码时代的到来,我们开始从未有过地“同化”,却又史无前例地“分化”;胶片死亡后,我们将“凭空捏造”认作真实,电影还是电影吗?
限于篇幅,我不能一一列举书中谈及的社会历史议题:国产电影《钢的琴》对下岗一代如何记忆叙事,东西方对于《末代皇帝》不同的观感视角体现了怎样的历史观,近几年的好莱坞大片《规则改变》《总统杀局》《关键选票》《大而不倒》又怎样体现和左右美国大选及资本救市。其中尤为精彩的是以电影《卡洛斯》为例对当下的恐怖主义题材的阐释。
几乎可以毫不犹豫地说,上世纪70年代起,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以降,好莱坞电影或多或少为国际恐怖主义行动提供了想象的天际线和范本。戴锦华谈及一则个人经验,“‘9·11’袭击发生时,我坐在电视机前,目击了第二架飞机撞向双子大楼,直到大厦轰然坍塌。当时一个怪诞的感觉是,这一场景似曾相识。这以后,我试图追问这种感觉的由来,结果答案相当简单:来自好莱坞灾难片《独立日》。其中袭击轰炸的场景,是极为接近、几乎是同一机位拍摄的画面。”
今天讨论恐怖主义电影时,人们主要的诉求是借助这些影片去重新叩访冷战的历史,而不是进一步封闭和遮蔽那段历史。许多宣扬“民族解放”的追随者在坚持中被国际困境推向了自己信念的反面。事态每况愈下,找不到出口的民族斗士卡洛斯变为国际雇佣军,与“恐怖”合流,最终蜕变为恐怖主义意识形态所勾勒的恐怖分子。“我们也可以在其他影片中看到欧洲左翼激进行动派如何在腹背受敌、自我背叛中崩解和毁灭。我以为,这批影片呈现与纪录的意义正在于此。”
对话尝试从政治性内涵的角度触碰电影与社会,即屏中现实与屏外(屏后)的世界,添加的参数是与历史相对、与历史相关的记忆。二人由屏外的世界而入屏中的影像,探讨影像的历史与历史的影像;而后破镜而出,再度尝试回应或对话现实。所构成的电影文本细读与思考不再是单个艺术领域的闭环,而是有机的,与社会、经济、人文相观照联结的流动过程。从社会而来又反哺社会与人心,这一直是戴锦华近几年热衷且深入钻研的批评模式,其中的旁征博引与疏朗开放的精神令人振奋。
走出洞穴的人,后来呢
来到科技这个维度,话题变得更为混沌无力。
电影在英语中至少有三种表述:Film、Movie和Cinema——道出三种不同视角的理解。Film强调电影的物质材料,即对象世界成像于化学胶片之上。Movie更强调动态的影像,或说“活动的照片”,是电影的特征。而Cinema则表达放映的空间——在剧院这个公共场所,完成审美与社会仪式,它具有联系共同体认同的功能。称电影为20世纪的世俗神话甚至是“世俗宗教”,其出发点正是源自影院空间。影院观影是一种社会文化行为,观众背后的放映机窗口投射影像到前方的银幕上,由此出现了20世纪的电影艺术和柏拉图的“洞穴神话”的类比。影院的魅力在于召唤人的集聚,它是一个同质与异质的身体相遇的地方,但集体的观影行为伴随着个人隐秘的、对银幕上想象的占有,是一份共享的又极度私密的心理体验。同时,现代电影理论的核心变化之一,就是以“镜”“镜像”取代“画框”与“窗”,成为讨论影像与观影经验的关键词。
于是,人们对电影(影院)的迷恋,既是某种心理症候——重返生命的“镜像阶段”,即混淆了真实与虚构、自我与他者,又是某种有效的心理疗愈——在影片的大团圆与种种想象性解决中得到抚慰与补偿。随着胶片时代的终结,数字时代的电影打破的正是这样的空间,电影与影院的分离已经开始发生了。电影银幕、影院空间开始碎片化,散落在电脑、手机等诸种“黑镜子”上。
坐在洞穴里的人尚可以设想一个无边无际的自由宇宙,但是真的走出去了,又该如何?正如《西蒙妮》里的那句台词,“当人们创造虚假的能力已经超出人们辨别真假的能力时,电影不再需要‘人’了”。这是一个无比哀伤的隐喻,但在戴锦华眼中,临界终结的时刻,新旧时代交界处恰恰有可能倒逼出新的文化选择,人们依然有可能选择回归,因为人永远需要心灵有个出口,“这几乎像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好莱坞工业以宽银幕史诗巨片回应电视冲击的21世纪版。”其同样的误区在于,影院的魅力始终不只是感官,更是心理效果。数码转型所改变的绝不仅是电影,而是整个文化生态,它或许会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仍名之为电影的影像艺术。电影对影院的归属仍然是质的规定,其外延与周边则愈加宽泛。唯有此,电影才能在影院空间中继续实践着独特的社会性:相遇与孤独的共享,黑暗的影院、光影的视窗、相邻的陌生人、孤独的人群所创造的心理效果,如此复杂层次的个体-集体心理经验依旧并非完备的家庭影院或小小的单个黑镜所可能取代。
数字时代为人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个人自由,但是自由的人们前所未有地被束缚在全球性的经济结构之中,有了所谓的“颅内高潮”“圈地自萌”,像极了吊在树上的一个个小小的蜂巢;而另外一方面,绝对的个人主义生存,本身并没有改变人类是高度社会化和组织化的事实。这是一个“个人主义绝境”,在这个层面上,电影洞穴的崩塌会带来什么,我们还无法确切评估,唯有一点:“电影是迄今为止,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窗口。只要你不是被单一的趣味所限定,从这个窗口望下去,这个世界上发生过的、正在发生的和即将发生的一切问题,都在你的视野里。”我想在今天,诸如此类的视野、对话与思考,多多益善。此外,二人还贡献了一份精彩纷呈的高品质电影清单,它们不仅是观点的支撑与注脚,更值得爱影人收藏品评。(庄加逊)
《返归未来》是电影学者戴锦华和王炎围绕电影议题所做的七次深度对谈,时间跨度长达六年。
通过鲜活犀利的思想碰撞,二人将个体记忆与银幕现实置于20世纪动荡多变的历史长流中,向读者揭示出作为特殊叙述文本的电影在“书写”与“呈现”的过程中带来的谜题、反思以及挑战。
专栏结集,尤其是对话体裁,易显得零散,需要调动读者更多的知识及经验储备才能产生代入感。但这本小书读来实在叫人痛快,爱影人心中的“戴爷”延续了她一贯的精准毒辣,在与王炎的文字交锋中重新发现了电影,做了别样的发问。
电影的要害,要害的电影
全书的一体成型归功于精彩的编辑,但更为要紧的核心是对电影惯性思维的打破。
人们常说电影是20世纪最伟大的艺术,“艺术”二字的强大光环无疑掩盖了它区别于其他传统人文艺术的两个维度,恐怕也是电影之所以成为电影的构成基因:政治性与科技性。
当然,电影可以拿来像绘画、音乐一般分析其创作手法、艺术风格,我们看过太多诸如此类的谈论电影艺术的书,无须赘述。事实上,在那篇沾满了前人唾沫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中,本雅明就触及了关窍,“人们耗费了不少精力钻牛角尖似的争论摄影到底算不算一门艺术,却没有先问问这项发明是否改变了艺术的普遍特性;而电影理论家也犯下了同样的错误,他们还在努力想让影像更接近于艺术。但这根本不是电影的核心”,“电影这种优越性有助于艺术与科学的互相融合,而这正是电影最重要的地方。当我们观察一个行为与特定的情况配合完美时(比如人体的肌肉运作),我们一点也不知其中的契合是属于艺术表现还是适于科学方面的探索。科学与艺术迄今往往各行其道,可是有了电影,我们可以说摄影的艺术发展与科学探索已结合为一体,这是电影的一大革命性功能”。
再往外延伸一些,政治与艺术品的展览价值有着极为密切、纠缠的关联,当科技、政治、展演三者合一,身为媒介的电影就此成为一个支点,甚至可以撬动整个地球。
看电影的人陷溺在“艺术与故事”中,忘记了从来没有一种艺术如此密切地仰仗科技,从来没有一种艺术可以如此真切地将世界与历史摆在你面前,也能将幻象变得真实,乃至成为改变你自身行为模式、操控历史与政治的书写。
基于这个角度,《返归未来》是第一次集中的、极具爆发力的关于电影政治内涵及科技性特质的聚焦,它告诉读者,我们关于电影的思考不该停留在感官的艺术呈现层次,那是很单薄的视觉误解。
从社会而来,反哺人心
戴锦华拿一个文字游戏比拟了银幕的“二律悖反”:
游戏的对象是“屏蔽”一词。我们在这个词组间加一道斜杠,变成“屏/蔽”。屏本意是遮挡与阻断,但在今日的语言系统中,它更多地对应英文中的screen——银屏、屏幕、视屏,“屏”意味着可见与看见。在电影理论中,电影银幕经常被转喻为窗、框中画,抑或是镜子。当我们着魔般地凝视着屏幕,似乎从无数扇窗口望去:我们看见,我们获知,我们发现。于是,我们忽略了甚至遗忘了屏之本意。每个视窗都同时是一面屏;每一个(屏)显都同时是一次(遮)蔽;我们在看见的同时不见。
有了这个立足点,再来看电影,一切变得意味深长:历史是权力的书写、胜利者的清单,同时也可以是个体记忆对既有历史的质疑与重写;好莱坞电影工业展现了美国政坛风雨,同时也反过来再造美国政界的姿态;究竟是恐怖主义促发了反恐题材电影的兴盛,还是电影创造了恐怖主义的想象;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完成以及数码时代的到来,我们开始从未有过地“同化”,却又史无前例地“分化”;胶片死亡后,我们将“凭空捏造”认作真实,电影还是电影吗?
限于篇幅,我不能一一列举书中谈及的社会历史议题:国产电影《钢的琴》对下岗一代如何记忆叙事,东西方对于《末代皇帝》不同的观感视角体现了怎样的历史观,近几年的好莱坞大片《规则改变》《总统杀局》《关键选票》《大而不倒》又怎样体现和左右美国大选及资本救市。其中尤为精彩的是以电影《卡洛斯》为例对当下的恐怖主义题材的阐释。
几乎可以毫不犹豫地说,上世纪70年代起,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以降,好莱坞电影或多或少为国际恐怖主义行动提供了想象的天际线和范本。戴锦华谈及一则个人经验,“‘9·11’袭击发生时,我坐在电视机前,目击了第二架飞机撞向双子大楼,直到大厦轰然坍塌。当时一个怪诞的感觉是,这一场景似曾相识。这以后,我试图追问这种感觉的由来,结果答案相当简单:来自好莱坞灾难片《独立日》。其中袭击轰炸的场景,是极为接近、几乎是同一机位拍摄的画面。”
今天讨论恐怖主义电影时,人们主要的诉求是借助这些影片去重新叩访冷战的历史,而不是进一步封闭和遮蔽那段历史。许多宣扬“民族解放”的追随者在坚持中被国际困境推向了自己信念的反面。事态每况愈下,找不到出口的民族斗士卡洛斯变为国际雇佣军,与“恐怖”合流,最终蜕变为恐怖主义意识形态所勾勒的恐怖分子。“我们也可以在其他影片中看到欧洲左翼激进行动派如何在腹背受敌、自我背叛中崩解和毁灭。我以为,这批影片呈现与纪录的意义正在于此。”
对话尝试从政治性内涵的角度触碰电影与社会,即屏中现实与屏外(屏后)的世界,添加的参数是与历史相对、与历史相关的记忆。二人由屏外的世界而入屏中的影像,探讨影像的历史与历史的影像;而后破镜而出,再度尝试回应或对话现实。所构成的电影文本细读与思考不再是单个艺术领域的闭环,而是有机的,与社会、经济、人文相观照联结的流动过程。从社会而来又反哺社会与人心,这一直是戴锦华近几年热衷且深入钻研的批评模式,其中的旁征博引与疏朗开放的精神令人振奋。
走出洞穴的人,后来呢
来到科技这个维度,话题变得更为混沌无力。
电影在英语中至少有三种表述:Film、Movie和Cinema——道出三种不同视角的理解。Film强调电影的物质材料,即对象世界成像于化学胶片之上。Movie更强调动态的影像,或说“活动的照片”,是电影的特征。而Cinema则表达放映的空间——在剧院这个公共场所,完成审美与社会仪式,它具有联系共同体认同的功能。称电影为20世纪的世俗神话甚至是“世俗宗教”,其出发点正是源自影院空间。影院观影是一种社会文化行为,观众背后的放映机窗口投射影像到前方的银幕上,由此出现了20世纪的电影艺术和柏拉图的“洞穴神话”的类比。影院的魅力在于召唤人的集聚,它是一个同质与异质的身体相遇的地方,但集体的观影行为伴随着个人隐秘的、对银幕上想象的占有,是一份共享的又极度私密的心理体验。同时,现代电影理论的核心变化之一,就是以“镜”“镜像”取代“画框”与“窗”,成为讨论影像与观影经验的关键词。
于是,人们对电影(影院)的迷恋,既是某种心理症候——重返生命的“镜像阶段”,即混淆了真实与虚构、自我与他者,又是某种有效的心理疗愈——在影片的大团圆与种种想象性解决中得到抚慰与补偿。随着胶片时代的终结,数字时代的电影打破的正是这样的空间,电影与影院的分离已经开始发生了。电影银幕、影院空间开始碎片化,散落在电脑、手机等诸种“黑镜子”上。
坐在洞穴里的人尚可以设想一个无边无际的自由宇宙,但是真的走出去了,又该如何?正如《西蒙妮》里的那句台词,“当人们创造虚假的能力已经超出人们辨别真假的能力时,电影不再需要‘人’了”。这是一个无比哀伤的隐喻,但在戴锦华眼中,临界终结的时刻,新旧时代交界处恰恰有可能倒逼出新的文化选择,人们依然有可能选择回归,因为人永远需要心灵有个出口,“这几乎像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好莱坞工业以宽银幕史诗巨片回应电视冲击的21世纪版。”其同样的误区在于,影院的魅力始终不只是感官,更是心理效果。数码转型所改变的绝不仅是电影,而是整个文化生态,它或许会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仍名之为电影的影像艺术。电影对影院的归属仍然是质的规定,其外延与周边则愈加宽泛。唯有此,电影才能在影院空间中继续实践着独特的社会性:相遇与孤独的共享,黑暗的影院、光影的视窗、相邻的陌生人、孤独的人群所创造的心理效果,如此复杂层次的个体-集体心理经验依旧并非完备的家庭影院或小小的单个黑镜所可能取代。
数字时代为人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个人自由,但是自由的人们前所未有地被束缚在全球性的经济结构之中,有了所谓的“颅内高潮”“圈地自萌”,像极了吊在树上的一个个小小的蜂巢;而另外一方面,绝对的个人主义生存,本身并没有改变人类是高度社会化和组织化的事实。这是一个“个人主义绝境”,在这个层面上,电影洞穴的崩塌会带来什么,我们还无法确切评估,唯有一点:“电影是迄今为止,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窗口。只要你不是被单一的趣味所限定,从这个窗口望下去,这个世界上发生过的、正在发生的和即将发生的一切问题,都在你的视野里。”我想在今天,诸如此类的视野、对话与思考,多多益善。此外,二人还贡献了一份精彩纷呈的高品质电影清单,它们不仅是观点的支撑与注脚,更值得爱影人收藏品评。(庄加逊)
本文来源:解放日报责任编辑:庄加逊
免责声明:
1、凡本网注明“来源:***(非中国警营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的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2、如因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需要同本网联系的,请在30日内进行。
相关阅读
- 2023-05-15电影《京门烽火》定档6月9日
- 2023-05-12大女主时代来了,先锋国剧《外婆的新世界》收获口碑和热度双高
- 2023-05-11《纵然》官宣开机 重磅打造跨越时空的勇敢奔赴
- 2023-05-10《长安三万里》发布定档预告 壮美大唐山河辽阔
- 2023-05-09《闪电侠》国内首波口碑出炉 全片高能掀好评狂潮
头条图文
热点推荐
精选图文
阅读排行榜
品牌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