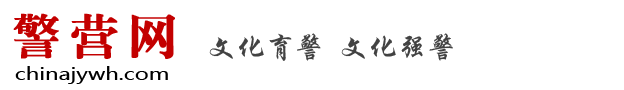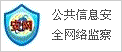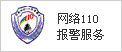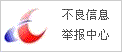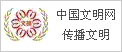吴作人:丹青简雅夺天工
作者:钱念孙(安徽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原主席、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员、安徽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学人小传
吴作人(1908—1997),祖籍安徽宣城泾县,生于江苏苏州。画家、美术教育家。1926年入苏州工业专门学校建筑系学习,后在上海艺术大学、南国艺术学院、中央大学学习,师从徐悲鸿。1930年考入法国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后转入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学院。1935年回国,任中央大学艺术系讲师。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中国美术会理事。1946年,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油画系教授兼教务长。新中国成立以后,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曾任中央美术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出版有《吴作人画选》《吴作人水墨画集》等画册,著有《吴作人文选》。
吴作人先生是20世纪中国美术事业开拓前行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人。他不仅自20世纪50年代起长期担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80至90年代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直接策划组织诸多美术教育和美协工作的重大事项;更以自己杰出的创作实绩和鲜明的个性风格,在当代中国画坛树立起既有深厚传统底蕴、又洋溢强烈时代精神的文化标杆,为探求中国美术如何立足民族文化基点吸收外来艺术优长跋涉前进,积累了足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知白守黑》 吴作人 绘

《藏原放牧》 吴作人 绘
西北之行:从油画转向国画
吴作人的美术创作,在油画和国画两个领域均有卓越成就。20世纪50年代以前,他主要以画油画为主,留下不少堪称经典的油画名作;50年代以后,虽然也有一些油画新作推出,但更多沉浸于国画写意之中。纵观近百年中国美术发展历程,不少著名画家都曾经历从早期画油画到中晚年转向国画创作的演变过程。如果说,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等是从油画转入国画的第一代杰出尝试者,那么,吴作人则沿着徐悲鸿等开创的援西入中的路径奋力开拓,是从油画转入国画创作的第二代出色代表。
吴作人早年追随徐悲鸿,20世纪20年代末曾先后在徐悲鸿任教的南国艺术学院美术系和中央大学艺术系学习。1930年春,在徐悲鸿的鼓励和帮助下,他考入法国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后转入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学院院长巴思天教授工作室深造。在比利时求学期间,他在皇家美术学院全校会考中,以油画习作《男人体》取得第一名,并获金质奖章和桂冠生荣誉,可见他对油画钻研之深和西画基本功之扎实。他此阶段创作的油画《哥萨克兵》《纤夫》《争论》《李娜肖像》等,具有典型的西欧传统写实主义油画的风貌,显示出坚实的素描基础和运用色彩的能力。1935年秋,应徐悲鸿邀约,吴作人告别巴思天教授,回国赴南京任中央大学艺术系讲师。不久,他和另一位艺术系讲师吕斯白以及杭州艺专教授刘开渠三人联合在中央大学举办画展,开始在艺坛崭露头角。1937年春,他又以《出窑》《玄武湖上的风云》等入选第二届全国美展,并当选为中国美术会理事。
1943年4月至1945年2月,吴作人用近两年的时间奔赴甘肃、青海、西康等地体验生活、采风写生。他参观成吉思汗陵,游览塔尔寺,深入玉门油田,观摩敦煌莫高窟并临摹壁画佳作,到达秦岭、康定、玉树、甘孜等地。西部辽阔、雄放、刚健、质朴的风土人情,令他称奇、让他感奋。他除了创作《祭青海》《漠上旋沙》《甘孜雪山》《负水女》《玉门油矿》等大批作品,沿途举办数次写生作品展,还以深厚的传统诗词功底,赋诗多首抒发襟怀。请看其《一九四三年出河西访莫高窟未是草》:
日上三危射九重,长林萧瑟动金风。
云杳磬咽喑精舍,幢劫经残绝密宫。
千载神工依断壁,万龛变相没秋蓬。
历朝失道启边寇,欲罢丹青试引弓。
这首七律不仅刻画出莫高窟的景象,更表达了作者感叹国家磨难,世事沧桑,自己很想弃笔从戎,报效祖国(“欲罢丹青试引弓”)的心境。
西北之行对吴作人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包括后来从油画向国画转变,都产生不可低估的重要影响。他晚年在回忆录《艺海无涯苦作舟》中说:“艰辛的征程,不但磨炼了我的意志,更磨炼了我的画笔。”这种对画笔的磨炼,主要体现在其创作风貌发生明显变化上。将他1932年在比利时留学时所作油画《纤夫》,与此次西北之旅所作油画《负水女》比较,同样是描绘野外人物题材,但风格却大不相同:后者显然色彩更为明亮,线条更加轻快流利,几近平涂的色块运用更多;北欧含蓄深沉的光色被中国西北高原强烈光照所取代,伴随弗拉芒画派因素的减弱,追求简练、概括的中国传统绘画韵味明显增强。不论是油画还是水彩及速写,不论是人物、风景或主题创作,他此后的作品线条运用明显增多,薄涂的色彩更加灵动,画面整体感更强,更加讲究神韵。徐悲鸿当年在《吴作人画展》一文里,谈论其西北写生的收获说:“作品既富,而作风亦变,光彩焕发,益游行自在,所谓中国文艺复兴者,将于是乎征之夫?”这不仅肯定其“作风亦变”的改观和进步,而且期许甚高,认为他是“中国文艺复兴者”的希望所在。
吴作人油画创作的高峰在四五十年代。除了《负水女》《草原云雨》《镜泊湖》《孙中山与李大钊》等外,《三门峡》和《齐白石像》堪称代表作。《三门峡》画幅不大,但视野宏阔,场面浩大,将奔腾的黄河穿越崇山峻岭逶迤而来,激流中一块块巨石或横卧或屹立的壮丽景观,以及岸边和岛礁工地上支架林立、人头攒动建设水电站的繁忙场面,表现得既富有审美节奏和艺术感染力,又充盈高涨的建设热情和对生活的赞美咏叹,可说是风景画和主题创作完美结合的典范作品。《齐白石像》深得中国古代画论“以形写神”的要诀,耄耋老人安详庄重的坐姿,形成稳重、厚实、简括的构图;深青色棉袍、乌黑软绒帽以及灰调子背景,衬托老画家暖色调的鹤发童颜,使人物显得神采奕奕,气度非凡;尤其是对敏锐深邃的目光、习惯吮笔的嘴唇和右手捏笔姿态等细节的刻画,彰显了一代艺术大师的职业特点和将艺术融入生命、对艺术精益求精的精神。《齐白石像》的成功,当然得益于作者多方面综合素养和精湛的艺术表现能力,但注重吸收中国画营养和表现民族审美趣味,乃是不可忽视的原因。苏联普希金造型艺术馆馆长、美术鉴赏家扎莫希金当时看了该画,一方面称赞可与列宾的名作《托尔斯泰像》相媲美,一方面又指出其油画“是从中国人眼光来观察的,像中国画一样,单纯而富有诗意”。这点出了吴作人油画创作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在油画民族化道路上做出可贵探索、取得可喜成绩。
对油画民族化的求索,还引起他对表现工具与表现对象关系的思考。一方面,他认为国画主要使用水墨,更多用线条来勾勒形象,油画主要用油彩,更多以明暗块面来塑造物体,两者的工具和手法不同,但“不管是中国画还是油画,工异趣同”;另一方面,他感到“中国画的表现方式最切合中国人的思想感情,那是许多年以来在特定文化条件下形成的民族的、特有的美学风格和审美观念”。他解释为什么从油画转向中国画的原因说:“我自己觉得,在造型的提炼、取舍方面,我现在所采取的这种中国画方式比以前在油画上要求达到的东西更多。我自己觉得,用中国传统的工具技法表现,比较更能达到自己艺术创造的要求。”正是如此,吴作人自五十年代起在画油画的同时,不断尝试中国画创作,至六十年代特别是七十年代以后,油画只是偶一为之,国画逐渐成为他的主攻项目。他回归传统专攻国画后,不仅多种题材的国画佳作频出,更以鲜明的创作个性和独特的艺术风貌,赢得艺坛和各界的广泛关注与称赞。
开疆拓土:为国画注入新意
吴作人的中国画创作不蹈故常,一出手就别开生面:不论在表现对象的选择,还是在绘画语言的锻造上,他都以自己的睿智和见识,走出一条既迥异于古人又有别于今人、既富有个性色彩又饱蕴时代精神的独特道路。
从表现对象上看,他画得较多的牦牛、骆驼、熊猫等,都是以前中国画没有画过或绝少涉猎的,这反映他步入国画园囿之初,就决意不走别人走过的老路而要另辟蹊径,要给画坛创造新的形象、带来新的意趣。有些作品的表现对象如鹰隼、金鱼、鸽子等,虽然已经有人描绘,但他以自己的构图、形象和笔墨予以呈现,同样给人耳目一新的审美享受。
能够做到这一点,与他清醒的创新意识和个性追求密不可分。他认为,一个艺术家在人生观上可以“无我”,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跟风随大流;但在艺术观上一定要“有我”,艺术创作必须要有自己的东西,即自出机杼、别具一格、自成一家,必须以某种独创性呈现自己的面貌。艺术创作只有“有我”,哪怕处于相同时代、所画题材相似、表现手法相近,不同的艺术家也可以“各异其趣,各尽其妙”。如何做到“有我”?画家不仅要找到自己的表现对象,还要在对象中寄寓和传达自己的思想情感。对此,吴作人以画骆驼为例,谈了自己体会:
比较起来,我多是画古人画得少的东西。我见过画骆驼的不多。据我自己的认识,骆驼自有它独特的性格。戈壁滩上的骆驼能够负重致远,不畏艰苦,跟牦牛那样雄强与猛冲不同,它是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它的造型也很有特点,从头、脖子、驼峰到腿,给人以坚毅而厚重的感应。尤其到寒天降临时,它长了新毛,一群群站在沙丘里或是在戈壁滩上行走,使人激动得不禁体验到一种不平凡的力量……从动物本身说来,这是它的特性;对人说来,能把人带到一个与环境奋斗的境界,一个既是诗,是音乐,又是画的境界。人得向它学习。所以我爱画骆驼,就是想充分表现这么一种性格所兴起的画境。(《客有问——谈师造化、夺天工》)
吴作人的国画作品,之所以给人“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颖之感,不仅在于他对传统国画的表现领域开疆拓土,塑造了骆驼、牦牛、熊猫等一系列新的形象,还在于他对这些动物深入观察、研究、体悟,从中捕捉与人性相通的某种活跃的生命精神,在艺术形象中注入自己的独到感受和思想情怀。正如他自己所说,他画动物不是要表现品种,不是搞动物志、作图谱,而是“托物言志”,借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他画的骆驼,不论是50年代的《任重踏千程》,还是70年代的《极目千里》等,其中无不寄寓着坚韧不拔,负重远行的美好情愫。这既是对骆驼本身特点的揭示和表现,也是对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不断跋涉向前精神的写照和颂扬。
从根本上说,绘画无非是要解决“画什么”和“怎么画”的问题。吴作人除了在画什么上不落窠臼,推陈出新,还在怎么画上孜孜以求,别树一帜。与一般国画家不同,他是在西画达到很高造诣、在画坛拥有较高地位(担任中央美院院长)的情况下,转而从事国画创作的。这时,他不仅对绘画艺术本身已有深厚积淀和深刻理解,而且对如何在高手如云的国画原野跑马圈地,有了更多的考量和准备。
从“怎么画”的角度看,吴作人国画创作最值得注意的特点是“简雅”。所谓“简”,就是简练概括,举要治繁,以“少少许”胜“多多许”。所谓“雅”,就是正规文雅,如郑玄《〈周礼〉注》所说:“雅,正也,古今之正者,以为后世法。”他谈论中国画创作说:
我以为艺术品的好,应是完整的、能通过简练的形象充分表现内容,用最简练的语言表达最充分的感情。中国美术的优秀传统特点在于简练中充分传出神韵,笔墨少而意境充分。充分不等于繁琐,简练不是简单。无限制地加工并不就是好。(《在中国画创作组谈人物画的刍见》)
他在《谈中国传统绘画的欣赏》里,曾将郎世宁画树与齐白石画荷对比说:“画树不是去一笔笔仔细描摹自然,而要能寥寥几笔勾出树的风度,写出树的性格。意大利人郎世宁也画中国画,将每枝每叶画得很周全,而画意呆痴。”“白石画残荷,常常是深思熟虑去构思荷秆的布局,因此荷秆荷叶交错,多而不乱,少而不单调,笔力苍劲、挺拔。”他归纳徐悲鸿国画成功的缘由说:“要加强表现力,就得大胆取舍;为了引人入胜,需要为观众留有余地。言简意赅,笔不到而气韵横溢,虽弦绝而余响,却‘此时无声胜有声’,反而是艺术的充实。这使我们领悟到从事艺术制作,并不以无限加工为求‘精’,无休止刻画以致‘真’。轻描淡写,墨饱笔酣,纵情挥洒,同可称神功。”吴作人常画牦牛等,画面处理多半极为简要。如名作《藏原放牧》,四条奔牦虽处近景中心位置,但高度概括,几乎没有细部刻画,用笔用墨酣畅淋漓又收拾精当,把牦牛奔跑的姿势和空间层次等表现得恰到好处。远处的放牧人及牛群等,轻描淡写,远远推开,画面极为广阔,却主体突出,可谓秉一总万,用宏取精,言简意赅,境界博大。吴作人说:“我画牦牛并不重在它的具体形态如何,而主要在于它的性格、它强有力的体态、迅捷的速度。不必去仔细描摹它的眼睛、犄角怎么长。那些问题也都是需要知道的,无知是不行的,但艺术的表现力并不在把自己的知识全盘托出……我这样画,为的是体现出一种雄强有力的运动,也是一种雄强有力的艺术境界,想使人看了感到有一种推动的力量,从而发生共鸣。”
吴作人的国画形式简约,常常典雅含蓄,寓意深刻,甚至饱蕴思辨性哲理。如他画过多幅以鸽子为题材的作品,其中一幅名为《知白守黑》,画面只有一黑一白,一侧面、一正面两只鸽子,放在中下部,其余部分大片空白,左上角题有篆书标题和行书落款。“知白守黑”语出《老子》:“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原意表达古代道家虚静无为的处世态度,即虽知晓明白,当守之以沉默,这才是大家应遵循的模式。后来文人书画家把它运用到画论和书论中,指虚实互补,黑与白相反相成等形式规律。这幅作品以异常简洁明了的构图和形象,生动诠释中国书画奥妙无穷的计白当黑和黑白互济的辩证思想,以至表达了有无相生、得失相随的哲理。吴作人的一些国画作品,画面单纯洗练,既有很强的形式感,又包孕丰富的思想蕴涵,读来给人悦心明智的审美意趣。
取得如此艺术成就,关键在于他十分讲究作品的“立意”,即中国传统画论所说的“意在笔先”。他曾强调,“不先立意就不足言绘画艺术”。一件艺术创作如果没有主观意愿即立意,必然枝枝节节不得要领。绘画需要“取舍”,但取什么、舍什么,要害还在“能立意就知道取舍”。就此而言,吴作人不仅是一个技巧全面、画艺高超的巨匠,还是一个勤于思考、善于立意、擅长以精练绘画语言表现深邃丰富思想的大师。
打通中西:下笔就是造型
近百年中国美术发展,离不开“西风东渐”“中西碰撞”的大背景。众多美术家都希望在打通中西、融汇古今的艺术旅程上,留下自己的足迹、耸立自己的丰碑,可真正如愿以偿者凤毛麟角。吴作人的美术实践,除了在油画民族化的道路上颇多尝试和建树外,在如何吸收西方美术优长提升中国画的表现力和形式感,以及如何看待中国画笔墨等问题上,都留下可贵的探索和宝贵的经验。
吴作人十分欣赏“师造化”“夺天工”两句古语,认为把这两句话结合起来,可以较好解答艺术创造中客观与主观的关系问题。造化和天工都是指外界自然形象,也可说是作品的表现对象。“师”就是要掌握自然物象的形态和结构,认识其形象的内在特点及寓意;“夺”就是要超过它,以表达自己想要的更高的艺术境界。他指出:“只知道‘师造化’,不知道‘夺天工’,就要走向一种极端,就是去当自然的奴隶。只知道‘夺天工’,没有‘师造化’的基础,就会走到另一个极端,就是走向非形象的穷途。”吴作人虽然强调“夺天工”,并非鼓励脱离形象的任意妄为,而是主张在尊重客观对象自然形态的前提下,进行加工、提炼、夸张、变形,以达到更典型、更集中表现对象的目的。
为此,他就中国画的笔墨问题提出一个十分值得重视的观点,即“下笔就是造型”。他说:“中国画的笔墨非常巧妙,巧妙得一下笔就是造型。”当然,国画有写意与工笔之分。工笔作画有一定的步骤,如描稿、勾线、淡墨、花青渲染、着色等,是有些工艺性的创造。“写意画不同,下笔就是造型,每一次下笔都不能重复。”他以自己切身经验为例说:“比如画熊猫,两点黑的眼睛就要研究,不能太方、太圆,也不能太平均、太重。耳朵也是非尖非圆,这里面都完全要运用书法。一笔下去,造型自然而然出来。”他画金鱼,不论是鱼头、鱼身、鱼尾,都是一笔下去,既有准确生动的形态,又有笔墨变化的趣味。其他如牦牛、骆驼、熊猫、鸽子、鹰隼等等,均以栩栩如生的形象和积极温婉的意蕴打动人的同时,又以墨饱笔酣、浓淡枯润的笔墨变化之美及其丰富的表现力,耐人咀嚼和玩味。
吴作人关于写意国画“下笔就是造型”的睿识和实践,对匡正中国画嬗变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偏颇,促进国画艺术守正创新健康发展,起码在两个方面别具意义和启示。
其一,对文人画忽视造型的纠偏。中国画演进到宋代,文人画悄然萌生,至明清已蔚为大观,当代仍势头不减。文人画家,历来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重视学养情怀,讲究技法和造型的“功力型”画家;一类是强调抒发性灵,轻视技法和造型的“逸笔型”画家。按理说,前者发展更全面,应该更受推崇;但实际上,后者往往被抬得更高,以至其轻薄画技和造型等弊端时常被忽视乃至漠视。如影响很大的陈衡恪《文人画之价值》一文就说:“何谓文人画?即画中带有文人之性质,含有文人之趣味,不在画中考究艺术上之功夫,必须于画外看出许多文人之感想。此之所谓文人画。”这里把“不在画中考究艺术上之功夫”,看作文人画的特质,自然助长那些怠慢技艺、轻薄造型、任意涂抹、以丑怪为能、以荒率为美现象的产生。吴作人提出“下笔就是造型”,将写意国画的笔墨之趣与造型之功结合起来,既符合包括文人画在内的国画创作的实际,又对有些文人画无视画技和造型等偏弊不乏矫正作用,对中国画的健康发展颇有积极意义。
其二,对中国画笔墨争论的启示。笔墨是中国画论里的老话题:南朝谢赫提出的“六法”中,就说到“骨法用笔”;唐末大画家荆浩创“六要”说,对“笔墨”概念作了直接阐述;此后“笔墨”逐渐成为中国画技法的代名词,也成为评价一幅国画高下优劣的重要标准。近代以来,西风东渐,传统国画如何创新发展?笔墨于中国画的价值如何?讨论一直此伏彼起,争议不断。前些年,吴冠中发表文章,标题就亮明观点《笔墨等于零》,基本否定笔墨的独立价值。张仃推出《守住中国画的底线》,肯定笔墨的重要意义,并借用黄宾虹的话说“中国画舍笔墨无其它”。其实,孤立地否定或肯定“笔墨”都难免出现偏颇。吴作人的“下笔就是造型”可谓一语破的,既明确中国画笔墨对塑造形象、构成画面的基础性作用,又包涵着对笔墨功力、技巧等所表现出来的形式美的欣赏和推崇。他以自己的切身经验指出,“中国画的笔墨有高度的表现力”,但笔墨之美“不是轻而易举的,不是信手拈来的,或者说,好像信手拈来,其实是经过长期的艰苦实践才能获得”。
因此他特别强调:“我很赞成写点字,篆、隶、楷、草都行,基本上还是篆、隶,篆、隶必须中锋,颜体楷书也是多用中锋,中锋本身包含着含蓄的力量。”“中国书法的每一笔都是在锻炼下笔就造型,这也是中国画下笔造型的一个前提。”画写意画如果没有书法基本功,许多造型如齐白石画的虾、鸟等,不可能几笔下去就生动呈现出来,而只会依样画葫芦地死描,那样必然呆板僵硬,不可能做到气韵生动。吴作人转向国画创作后,每日临池不辍,于篆、楷、行都下过功夫,将篆书庄严雄强的气势和行书活泼灵动的仪态相结合,在由篆入行上变化出自己刚柔相济、秀中见骨的自家风貌。在中华传统文化的系统里,书画既同源也同理。对书法的深入钻研,不仅有助于提高写意国画下笔就造型的技巧,而且书法关注整体效果、黑白处理、疏密关系,以及字的结体变化等,对于画面的意匠经营等都有启发意义。他画的一些牦牛、骆驼、隼鹰等,不着色,全用水墨,既笔墨酣畅又造型精妙,既简练概括又气韵生动,既有国画的美感又有书法的意趣。
吴作人具有广博文化知识和深厚艺术修养,经过严格技巧训练并拥有很强造型能力,稔熟国内外美术历史也了解当代中国绘画状况,深知自己艺术气质并善于发挥个性才华。他不追慕时尚,也不高标逸世;不愤世嫉俗,也不随波逐流;不故作高深,也不平淡天真。他始终以自己丰赡的学识和温文尔雅的态度,以简约而有内蕴的笔墨和形象,表现刚健清新的生命和气象,形成风清骨峻的简雅风韵和巧夺天工的审美意趣。这正是他人生修养和处事风度的自然流露,也是他以鲜明的个人风格丰富和提升中国书画品格的独到贡献。
《光明日报》( 2020年08月31日 11版)
本文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责任编辑:钱念孙
免责声明:
1、凡本网注明“来源:***(非中国警营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的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2、如因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需要同本网联系的,请在30日内进行。
- 2023-05-15爱国诗词研讨会走进澳门校园
- 2023-05-12爱国诗词研讨会走进澳门校园
- 2023-05-11毛泽东诗词:当代诗词改革创新的典范和指南
- 2023-05-10怀宁县三祝初中开展“传承优良家风,争做时代新人”主题演讲暨首届古诗词默写大赛
- 2023-05-09文学大咖云集浙江黄岩!共赴一场以橘花为名的诗词盛会
热点推荐
精选图文
阅读排行榜
品牌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