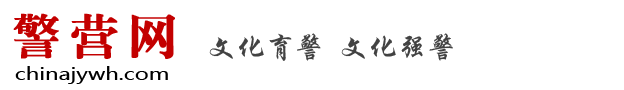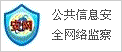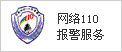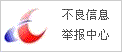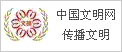雕塑中的浓浓乡愁
2020-05-26 17:06:40
来源:光明网-文艺评论频道
责任编辑:贺嘉年
乡愁,是二十世纪中国留洋知识分子的文化情结。文学作品则是抚平创伤的一剂良药。学者余虹在《艺术与归家》中这样说道:“现代人是一群离家出走的漂泊者。正因如此,现时代的诗与思都禀有一种天命或责任:引领人们归家。”而法籍华人艺术家、哲学家熊秉明选择以雕塑的形式,让一尊尊作品负荷起浓浓的乡愁。《关于罗丹:熊秉明日记摘抄》就记录了他青年时代修习雕塑艺术时的所见与思考。
熊秉明的雕塑生涯从师法西洋开始,最终达成融贯中西的境界。旅法之后,他首先修习哲学,一年之后转攻雕塑艺术,进入法国茹里安画院学习。在那里,他受到雕塑大师罗丹、布尔代勒作品的熏陶。在浪漫主义雕塑中,熊秉明逐渐体会到青年人身体与心灵的双重解放,寻找到艺术中美好而纯粹的生命情感。与此同时,启蒙导师纪蒙勤奋、严谨的工作态度,以及对弟子的朝督暮责,都使熊秉明逐渐意识到:雕塑不是对人体的机械解剖,不是自娱自乐的消闲工具,而是肩负着反映人类精神存在的崇高使命。
在诸多雕刻大师中,熊秉明格外中意罗丹,认为罗丹是现代雕刻史的第一人,是浪漫主义雕刻艺术的巅峰。熊秉明日记中,大部分篇幅都是对大师作品的鉴赏分析。在他看来,罗丹的作品是一部个人的史诗,不以和谐整一为美,而是要歌颂缺陷与痛苦:塌鼻子的人、臃肿的母体、枯槁的老妪、苍老的雨果等。正是在缺陷与脆弱中,人类才获得生存的意义。正因为生而不完美,人类才具备追求自由与永恒的权力。《地狱之门》就把人物的飞翔雀跃,勾勒得淋漓尽致;《青铜时代》则刻画出青春少年身心觉醒的刹那,塑造出少壮生命的仪态与心态,被诗人里尔克称为“行动的诞生”与“自我意识的觉醒”。
浪漫主义的核心是生命的悲剧感与英雄主义,正如庄子所言“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己”。当归于死灭的宿命不可逃脱,克服死亡的痛苦迸射生的欢歌,这就是艺术家的使命。《加莱义民》刻画了英法百年战争期间,法国加莱城六壮士为民请命捐躯的悲壮故事。在罗丹的作品中,这六位市民并不是面不改色、视死如归,而是集惊讶、怜悯、愁苦、怅惘为一体。正是从壮士们复杂的表情神态中,我们体会到了人生的意义。舍生取义,就愈显弥足珍贵。
在罗丹的所有作品中,熊秉明尤其钟爱《行走的人》,认为这座雕塑熔铸了浪漫主义的所有艺术观念。这是一尊无头无臂,只有双腿行走的身躯。其大步行走的姿态,就是人类的写照。它不知去向何方,我们也无法猜测它的表情与思想,但它面对未知的危险时,没有丝毫屈服与妥协。故国战乱,独在异乡,对自己与国家的未来充满迷惘。《行走的人》抚慰了熊秉明的乡愁情愫,让他领悟到赖以自豪的中华民族精神:大步前行,不惧前程,“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通过罗丹,熊秉明悟到了雕塑艺术的精髓。但是,他并非对前者全盘继承,而是融入了中国人的身份认知,扎根故土,立足现实。罗丹的雕塑作品,充满这样的现实关怀,展现出具体而鲜活的生命面对世界的情感万状。这是生命承载现实苦难的伟大与崇高,而非抽象、形而上学的喜怒哀乐。正如在1951年的一则日记里熊秉明所说:“罗丹的雕刻固然有强烈存在一直的显现,却并不表现静止的意志,抽象的意志,而是描写存在意志的实践经历,……罗丹之后,雕刻家不愿再背负太多、太重、太激动的狂情,他们如果悲哀,那是形而上学的悲哀;他们如果欢喜,那是纯存在的欢喜。”
身在西洋,心在东土,在熊秉明的艺术道路中,乡愁是一个无法跨越的羁绊。这种愁绪,在他学习之初就萦绕心头。在1948年的日记《法兰西的乡野》中,熊秉明阅读罗丹歌颂法兰西乡野的文字,心中油生黍离之思:“我不能不想到我的故乡了”。一年之后,他与三位即将学成归国的挚友寿观、道乾、文清作别,自己却因学习尚未告一段落而决定留下,与返乡失之交臂。在日记里,他流露出从此孑然一身的孤独。
在雕刻功力大有长进时,熊秉明面对西方同侪的赞扬却显得错愕失落。因为他发现,自己的作品弥漫着欧洲、拉丁气息,甚至比本土艺术家的雕塑更有风味,却也在这种“神似”中失去了中国风格。“在这里学习的目的不是欧化、西化,在这里继续这样做下去,能找到自己的道路吗?每天盯着西方女人裸体团团观察,看了又看,能做出中国雕塑吗?”由此,熊秉明与恩师纪蒙分道扬镳,乡愁成为他创作的源泉动力。故乡的场景夜夜袭来。他想起了昆明凤翥街茶点里马锅头的紫铜色面孔,想起了母亲的笑靥,想起了故乡形形色色的面容:“那是属于我的造型世界的,我将带着怎样的恐惧和欢喜去迎接他们!”
《孟子•离娄下》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熊秉明正是怀着感念家国、谦和敦厚的赤子之心从事艺术创作。数年之后,他曾两次受巴黎克蕾尔画廊之邀。当时,此画廊凭借抽象主义艺术而盛极一时。但道不同不相为谋,熊秉明早已把乡愁寄寓在学术之中。他主动退出画廊转教中文,随后又潜心研究书法理论,举办书法班,并提出“中国文化的核心的核心是书法”的著名命题。
熊秉明写于上世纪80年代的组诗《教中文》,是一位古稀老人作为游子的悲叹与诘问:“请你告诉我/我究竟一天一天更像中国人呢/一天一天更不像中国人呢?”其实,早在1951年的日记里,我们早已发现了答案:“但是见到了汉代的石牛石马、北魏的佛、南朝的墓狮,我觉得我灵魂受到另一种刺激,我的根究竟还在中国,那是我的故乡。”
(作者贺嘉年系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2019级硕士研究生)
熊秉明的雕塑生涯从师法西洋开始,最终达成融贯中西的境界。旅法之后,他首先修习哲学,一年之后转攻雕塑艺术,进入法国茹里安画院学习。在那里,他受到雕塑大师罗丹、布尔代勒作品的熏陶。在浪漫主义雕塑中,熊秉明逐渐体会到青年人身体与心灵的双重解放,寻找到艺术中美好而纯粹的生命情感。与此同时,启蒙导师纪蒙勤奋、严谨的工作态度,以及对弟子的朝督暮责,都使熊秉明逐渐意识到:雕塑不是对人体的机械解剖,不是自娱自乐的消闲工具,而是肩负着反映人类精神存在的崇高使命。
在诸多雕刻大师中,熊秉明格外中意罗丹,认为罗丹是现代雕刻史的第一人,是浪漫主义雕刻艺术的巅峰。熊秉明日记中,大部分篇幅都是对大师作品的鉴赏分析。在他看来,罗丹的作品是一部个人的史诗,不以和谐整一为美,而是要歌颂缺陷与痛苦:塌鼻子的人、臃肿的母体、枯槁的老妪、苍老的雨果等。正是在缺陷与脆弱中,人类才获得生存的意义。正因为生而不完美,人类才具备追求自由与永恒的权力。《地狱之门》就把人物的飞翔雀跃,勾勒得淋漓尽致;《青铜时代》则刻画出青春少年身心觉醒的刹那,塑造出少壮生命的仪态与心态,被诗人里尔克称为“行动的诞生”与“自我意识的觉醒”。
浪漫主义的核心是生命的悲剧感与英雄主义,正如庄子所言“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己”。当归于死灭的宿命不可逃脱,克服死亡的痛苦迸射生的欢歌,这就是艺术家的使命。《加莱义民》刻画了英法百年战争期间,法国加莱城六壮士为民请命捐躯的悲壮故事。在罗丹的作品中,这六位市民并不是面不改色、视死如归,而是集惊讶、怜悯、愁苦、怅惘为一体。正是从壮士们复杂的表情神态中,我们体会到了人生的意义。舍生取义,就愈显弥足珍贵。
在罗丹的所有作品中,熊秉明尤其钟爱《行走的人》,认为这座雕塑熔铸了浪漫主义的所有艺术观念。这是一尊无头无臂,只有双腿行走的身躯。其大步行走的姿态,就是人类的写照。它不知去向何方,我们也无法猜测它的表情与思想,但它面对未知的危险时,没有丝毫屈服与妥协。故国战乱,独在异乡,对自己与国家的未来充满迷惘。《行走的人》抚慰了熊秉明的乡愁情愫,让他领悟到赖以自豪的中华民族精神:大步前行,不惧前程,“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通过罗丹,熊秉明悟到了雕塑艺术的精髓。但是,他并非对前者全盘继承,而是融入了中国人的身份认知,扎根故土,立足现实。罗丹的雕塑作品,充满这样的现实关怀,展现出具体而鲜活的生命面对世界的情感万状。这是生命承载现实苦难的伟大与崇高,而非抽象、形而上学的喜怒哀乐。正如在1951年的一则日记里熊秉明所说:“罗丹的雕刻固然有强烈存在一直的显现,却并不表现静止的意志,抽象的意志,而是描写存在意志的实践经历,……罗丹之后,雕刻家不愿再背负太多、太重、太激动的狂情,他们如果悲哀,那是形而上学的悲哀;他们如果欢喜,那是纯存在的欢喜。”
身在西洋,心在东土,在熊秉明的艺术道路中,乡愁是一个无法跨越的羁绊。这种愁绪,在他学习之初就萦绕心头。在1948年的日记《法兰西的乡野》中,熊秉明阅读罗丹歌颂法兰西乡野的文字,心中油生黍离之思:“我不能不想到我的故乡了”。一年之后,他与三位即将学成归国的挚友寿观、道乾、文清作别,自己却因学习尚未告一段落而决定留下,与返乡失之交臂。在日记里,他流露出从此孑然一身的孤独。
在雕刻功力大有长进时,熊秉明面对西方同侪的赞扬却显得错愕失落。因为他发现,自己的作品弥漫着欧洲、拉丁气息,甚至比本土艺术家的雕塑更有风味,却也在这种“神似”中失去了中国风格。“在这里学习的目的不是欧化、西化,在这里继续这样做下去,能找到自己的道路吗?每天盯着西方女人裸体团团观察,看了又看,能做出中国雕塑吗?”由此,熊秉明与恩师纪蒙分道扬镳,乡愁成为他创作的源泉动力。故乡的场景夜夜袭来。他想起了昆明凤翥街茶点里马锅头的紫铜色面孔,想起了母亲的笑靥,想起了故乡形形色色的面容:“那是属于我的造型世界的,我将带着怎样的恐惧和欢喜去迎接他们!”
《孟子•离娄下》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熊秉明正是怀着感念家国、谦和敦厚的赤子之心从事艺术创作。数年之后,他曾两次受巴黎克蕾尔画廊之邀。当时,此画廊凭借抽象主义艺术而盛极一时。但道不同不相为谋,熊秉明早已把乡愁寄寓在学术之中。他主动退出画廊转教中文,随后又潜心研究书法理论,举办书法班,并提出“中国文化的核心的核心是书法”的著名命题。
熊秉明写于上世纪80年代的组诗《教中文》,是一位古稀老人作为游子的悲叹与诘问:“请你告诉我/我究竟一天一天更像中国人呢/一天一天更不像中国人呢?”其实,早在1951年的日记里,我们早已发现了答案:“但是见到了汉代的石牛石马、北魏的佛、南朝的墓狮,我觉得我灵魂受到另一种刺激,我的根究竟还在中国,那是我的故乡。”
(作者贺嘉年系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2019级硕士研究生)
本文来源:光明网-文艺评论频道责任编辑:贺嘉年
免责声明:
1、凡本网注明“来源:***(非中国警营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的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2、如因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需要同本网联系的,请在30日内进行。
相关阅读
- 2023-05-15爱国诗词研讨会走进澳门校园
- 2023-05-12爱国诗词研讨会走进澳门校园
- 2023-05-11毛泽东诗词:当代诗词改革创新的典范和指南
- 2023-05-10怀宁县三祝初中开展“传承优良家风,争做时代新人”主题演讲暨首届古诗词默写大赛
- 2023-05-09文学大咖云集浙江黄岩!共赴一场以橘花为名的诗词盛会
头条图文
热点推荐
精选图文
阅读排行榜
品牌栏目